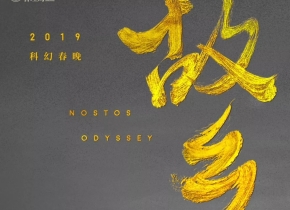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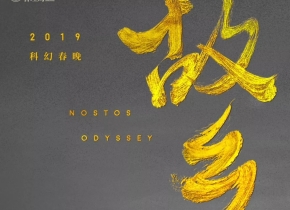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作者:【美】迈克尔·雷斯尼克
译者:月月鸟
插图:闲 人
编者按:
朴实简单的文字,波澜不惊的故事,仿佛真的出自一只智力超群的猩猩之口,讲述它的命运与爱恨,让人读后为之动容。
巴纳比坐在笼子里,等待萨利来实验室。
她会像昨天那样让它再做一次拼字游戏,但这回它不会令她失望了。它昨晚思考了整整一夜。思考很有趣。今天它一定能成功,到时候她准会开心地大笑,夸它聪明。它会躺在地上,而她会一边挠它的肚皮,一边说:“哦,你真是个小机灵鬼,巴纳比!”然后巴纳比会做个鬼脸,在地上打滚。
巴纳比就是我。
萨利走后,我有点孤独。天黑了,巴德会来打扫我的笼子,但他从不说话。他偶尔会忘记关灯,这时我就会试着同罗杰一家打招呼,但它们只是一群兔子,不懂手语。何况我也不觉得它们有多聪明。
每天晚上巴德来的时候,我总会坐起身,朝他微笑,做出“你好”的手势,但他没有一次答理过我。我觉得巴德跟罗杰一样傻。他就知道拍我的头。有时候,他会在离开的时候把“活动图片”开着。
我最喜欢的“活动图片”是弗雷德和巴尼①,但图片太亮,也播放得太快了。我常常央求萨利把迪诺带到实验室来同我玩儿,但她从没答应过。我喜欢巴尼,因为同弗雷德相比,巴尼的个头小,说话声音也小,跟我一样。而且,我的名字是巴纳比,听起来与巴尼差不多。天黑后,我陷入孤独,这时我会偶尔想象自己是巴尼,想象自己没有睡在笼子里。
这天,实验室外面一片白色。萨利进屋的时候,身上还沾着白色的碎片,但很快就融化了。
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玩具,上面长着许多小玩意儿,看起来就像大大的葡萄粒,跟博士桌子上的那个东西很像。萨利告诉我,她会给我看些图片,而我要敲出表示图片上的物件的葡萄。她给我看了一只鞋、一只球、一个鸡蛋、一颗星星,还有一个方块。
我没有把鸡蛋和球敲出来,但明天我会成功的。我每天都会思考更多的东西。就像萨利说的那样,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机灵鬼。
我们同新玩具玩了很多天,现在我只需要敲出正确的葡萄,就能同萨利说话了。
萨利会走进实验室,说:“今天早上怎么样啊,巴纳比?”我会敲敲葡萄,说:“巴纳比很好。”或者:“巴纳比饿了。”
我其实想说:“巴纳比很孤独。”但没有葡萄表示“孤独”。
今天,我用葡萄拼了一句话:“巴纳比想出去。”
“到笼子外面去?”萨利问。
“去外面。”我打手势说,“去白色世界里。”
“你不会喜欢外面的。”
“我不喜欢一个人待在黑暗里。”我说,“我会喜欢白色世界的。”
“外面很冷。”她说,“你会不习惯的。”
“白色很漂亮。”我说,“巴纳比想出去。”
“上次我让你出笼子,你却把罗杰弄伤了。”她提醒我。
“我只是想抚摸它。”我说。
“你掌握不了力道。”她说,“罗杰只是一只兔子,你很容易就会伤害它。”
“这次我会很温柔的。”我说。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罗杰呢。”她说。
“我不喜欢罗杰,”我说,“但我喜欢抚摸。”
她把手伸进笼子,挠挠我的肚子,抓抓我的后背,但我感觉刚好一点,她就住手了。
“你该上课了。”她说。
“如果我做对了,你会带东西来让我抚摸吗?”我问。
“你想要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另一个巴纳比。”我说。
她神色忧伤,没有回答。
一天, 萨利带来了一本满是图片的书。我又闻又舔,后来才明白过来,她是让我看。
书里有很多动物,我觉得其中一个长得特别像罗杰,但它是褐色的,而罗杰是白色的。书里还有一只小猫,跟我透过实验室窗户看到的那只很像。还有一只小狗,博士有时会带狗到实验室来。但书里找不到迪诺。
然后,我看到一个男孩的图片。他的头发比萨利的短,没有博士的那么白——或者说,跟巴德的一样黄。但男孩在微笑,我想他一定有许多东西可以抚摸。
第二天早上萨利来的时候,我有一肚子关于图片的问题要问她。但我还没有开口,她就先问起我来了。
“这是什么?”她说,举起一张图片。
“罗杰。”我说。
“不,”她说,“罗杰是一个名字。这种动物叫什么?”
我用力回想,“兔子。”我最后说。
“很好,巴纳比。”她说,“那这又是什么?”
“小猫。”我说。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地辨认完了整本书上的图片。
“巴纳比在哪儿?”我问。
“巴纳比是猩猩。”她说,“书里没有猩猩的图片。”
我很想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别的巴纳比,它们是否也感到孤独。
过了一阵子,我又问:“我有爸爸和妈妈么?”
“当然有。”萨利说,“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上一代。”
“那它们到哪里去了?”我问。
“你爸爸过世了。”萨利说,“你妈妈住在一个离这儿很远的动物园里。”
“巴纳比想见妈妈。”我说。
“恐怕不行,巴纳比。”
“为什么?”
“它认不出你了。它已经忘了你的模样,就像你记不起它一样。”
“如果我见到它,我会说‘我是巴纳比’,然后它就会认出我了。”
萨利摇摇头,“它不会懂的。你很特别,但它不是。它不会打手势,也不会使用电脑。”
“它还有别的巴纳比么?”我问。
“我不知道。”萨利说,“应该有吧。”
“它跟别的巴纳比怎么说话?”
“它不说话。”
我思索了很久这句话的意思。
最后,我说:“但它会抚摸别的巴纳比。”
“是的。它会抚摸它们。”萨利说。
“那它们肯定很高兴。”我说。
今天,我要问更多关于巴纳比的问题。
“早上好。”萨利来到实验室后说,“今天感觉怎么样,巴纳比?”
“动物园是什么?”我问。
“动物园是动物生活的地方。”萨利说。
“我能透过窗户看到动物园吗?”
“不行。那里离这儿很远。”
我冥思苦想很久,才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巴纳比是动物吗?”
“是的。”
“萨利是动物吗?”
“从某个角度说,是的。”
“萨利的妈妈也住在动物园?”
萨利笑了,“不是。”她说。
“她住在笼子里?”
“不是。”萨利说。
我思考了一会儿。
“萨利的妈妈死了。”我说。
“不,她还活着。”
我感到无比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问萨利的妈妈与巴纳比的妈妈有何不同。我越是努力去想这个问题,就越找不到答案,而萨利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懊恼之下,我开始用拳头击打地板,罗杰一家被惊得跳了起来,博士也连忙跑进实验室查看究竟。萨利给了我一个小玩具,只要我一打它,它就会吱吱地叫。我很快便平息了怒火,同玩具玩耍起来。萨利同博士说了两句,博士笑着离开了。
“开始上课之前,你还想问点别的问题么?”萨利说。
“为什么?”我问。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巴纳比是猩猩,而萨利不是?”
“因为上帝就是这么创造我们的。”她说。
我莫名地兴奋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正在接近真相。
“上帝是谁?”我问。
她试着给出答案,但我再次陷入了困惑。
天黑了,屋子里又只剩我和罗杰一家。我坐在巴德打扫过的笼子里思考上帝。思考真的很有趣。
如果上帝创造了萨利,也创造了我,那他为什么不把我造得像萨利那样聪明?为什么萨利能说话,还能用手做那么多事,而我不行?
我左思右想,却找不到答案。我决定去见上帝本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忘了即使巴纳比也喜欢被抚摸。
萨利一进实验室,我劈头就问:“上帝住哪儿?”
“天堂。”
“天堂很远吗?”
“是的。”
“比动物园还远?”我问。
“还远很多很多倍。”
“上帝会来实验室吗?”
她笑了,“不会。为什么这么问?”
“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
“或许我能回答一部分。”她说。
“为什么我这么孤独?”
“因为你很特别。”萨利说。
“如果我不是这么特别,我能同别的巴纳比在一起么?”
“是的。”
“我从没有伤害过上帝,”我说,“为什么上帝把我创造得这么特殊?”
第二天上午,我让萨利给我讲讲别的巴纳比。
“巴纳比只是一个名字。”萨利解释说,“除你之外,还有很多猩猩,但我不知道它们当中是否也有叫巴纳比的。”
“什么是名字?”
“名字就是让你与众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的名字是弗雷德或者迪诺,我就会变得跟别的猩猩一样么?”我问。
“不会。”她说,“你很特别。你是名叫巴纳比的倭黑猩猩。你很有名。”
“有名是什么意思?”
“许多人知道你是谁。”
“人是什么?”我问。
“男人和女人。”
“除了你、博士和巴德,还有别的人?”
“是的。”
然后我们开始上课。但我今天的表现相当糟糕,因为我一直挂念着那个除了萨利、博士和巴德,还有更多的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入夜后,我仍在入神地思考是谁把这些人放出笼子的,甚至都忘了去考虑上帝的问题。一连很多天,我都没有再想起上帝。
我听见萨利在跟博士说话,但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博士总是说我们没有更多的快乐了,而萨利一个劲儿地强调巴纳比很特殊。他们还讲了许多我不明白的东西。
谈话结束后,博士离开了,我问萨利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快乐了。
“快乐?”她重复道,“你在说什么?”
“博士说我们没有更多的快乐了。”
她瞪着我看了好久,“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快乐了?”我又问了一遍。
“不是快乐,是经费①。”她说,“博士说的单词是经费,跟快乐不是一回事儿。”
“就是说,巴纳比和萨利还能快乐?”我问。
“当然啦。”
我躺在地上,给她做了个手势:“挠挠我。”
她把手伸进笼子挠我,但我看见她眼睛里水汪汪的。人不高兴的时候,眼睛里就会渗水。我假装咬她的手,还学小时候的样子,在笼子里蹿来跳去,但这次我没能把她逗笑。
我听见门后传来对话声。又是萨利和博士在交谈。
“我们不能把它送到动物园去。”博士说,“如果它给观众打手势,那不到一个月就会有无数人要求释放它。然后会怎样?它会落得什么下场?你忍心在马戏团里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吗?”
“我们不能因为它很聪明就毁灭它。”萨利说。
“那谁来照顾它呢?你吗?”博士问,“它现在才八岁。但等它性成熟之后,就会变成一只凶猛的成年雄猩猩,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到时候,它能轻而易举地把你撕成碎片。”
“它不会的。巴纳比不会这么干。”
“你的房东允许你收留它吗?你愿意牺牲未来二十年的宝贵光阴照顾它吗?”
“我们最早今年秋天就可能得到新拨下来的经费。”萨利说。
“现实点吧。”博士说,“就算有新经费拨下来,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在全国搞相同项目的有六家实验室,有的甚至取得了比我们更好的成果。你知道,巴纳比不是唯一一只学会使用冠词和形容词的猩猩——除它之外,还有一只二十五岁的大猩猩和三只十多岁的倭黑猩猩。没有理由认为有人会再为我们投钱。”
“但巴纳比不一样。”萨利说,“它会问抽象的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它有一次问你上帝是谁。但我看过录像了,是你先提上帝的。如果你先提迈克尔·乔丹,它准会问乔丹是谁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篮球产生了持久的热爱。”
“至少让我去跟委员会的人谈谈吧。给他们看看巴纳比的录像。”
“委员会的人知道倭黑猩猩长什么样。”博士说。
“但他们不知道倭黑猩猩是怎么想的。”萨利说,“或许我可以借此说服他们……”
“说服了也没用。”博士说,“资金枯竭了。现在每个科研项目的经费都在萎缩。”
“我求你了……”
“好吧,”博士说,“我来安排一次会议,但千万别抱什么希望。”
我从头听到尾,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今天天亮之前,我梦见了一个到处都是巴纳比的地方。此刻,我坐在角落里,紧闭双眼,试图在梦境的记忆消逝之前抓住一点零星的片段。
我们每天继续上课,但我看得出萨利很不开心,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惹她不高兴。
这天早上,萨利打开笼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我抱了很久。
“我有话要对你说,巴纳比。”她说。我发现她的眼睛又渗水了。
我敲了敲葡萄,说:“巴纳比喜欢说话。”
“这话很重要。”她说,“明天你就要离开实验室了。”
“我可以出去了?”我问。
“你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去动物园?”
“更远。”
我突然想起了上帝。
“我要去天堂?”我问。
她笑了,但眼睛里的水更多了。“还没有那么远。”她说,“你要去一个没有实验室和笼子的地方。你将获得自由,巴纳比。”
“那个地方会有别的巴纳比么?”
“是的,”她说,“那儿有别的巴纳比。”
“博士错了。”我说,“萨利和巴纳比会更快乐的。”
“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她说。
“为什么?”
“我必须待在这儿。这儿是我的家。”
“如果你乖的话,或许上帝也会让你出笼子去的。”我说。
她发出一声古怪的呻吟,又抱住了我。
他们把我装进一只更小的笼子,里面没有灯。足足两天的时间,我闻到的都是臭味。喝下去的水大都吐了出来,外面的噪声刺得我耳朵生疼。有时候听得见人谈话的声音,一个既不是巴德也不是博士的人负责我的饮食。食物和水都是从笼子顶部的一个小洞送进来的。
我碰了碰他的手,想告诉他我没有生气。他尖叫着把手抽走了。
我不停地打手势:“巴纳比很孤独。”但笼子里黑黢黢的,没有人看得见我的手势。
我不喜欢这个新世界。
第三天早上,他们挪动了笼子,接着又挪了几次。最后他们把笼子提起来,带到一个地方,放下。我闻到了以前从未闻过的气味。
他们打开笼门,我走出来,踩在青草上。阳光夺目,我忍不住眯起了眼,看着那些既不是萨利、也不是博士或巴德的人。
“你到家了,孩子。”其中一个人说。
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番。这个世界比实验室大多了,我很害怕。
“去吧,伙计。”另一个人说,“到处嗅嗅,习惯一下新家。”
我到处嗅了嗅,但没有习惯这个新家。
我在这个世界里过了很多天。我熟悉了这里的树木、草丛,以及周围宽大的围栏。他们用水果、树叶和树皮喂我。我不习惯这些食物,有一阵子我病了,但后来又好了。
我听见这个世界之外的许多声音——尖叫、低吼、嘶鸣,我闻到许多陌生动物的味道,但我没有听见也没有闻到巴纳比。
一天,我又被装进了笼子。我孤零零地待了很久,然后他们打开笼子,我发现自己又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的树木高大繁茂,我几乎看不见头顶的天空。
“好了,伙计,”一个人说,“我们把你带到森林来了。”
他对我做了个手势,但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用手语回答说:“巴纳比很害怕。”
那人拍了拍我的头。这是我离开实验室后,第一次有人主动触碰我。
“好好生活去吧。”他说,“生一大群小巴纳比。”
然后,那人爬进他的笼子,笼子从我面前滚走了。我试着去追,但它移动得太快,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回头望着森林,听见那里传来古怪的声响。一阵微风带来水果香甜的气息。
我周围没有一个人,但我还是做了一个手势:“巴纳比自由了。”
巴纳比自由了。
巴纳比仍旧孤独。
巴纳比还很害怕。
我学着寻找水源,攀爬树木。我看见长有尾巴的小巴纳比同我叽里呱啦地嚷着什么,但它们不懂手语。我还看见浑身斑点的大猫。它们的叫声难听死了,我总是远远地躲着它们。
我希望我还待在实验室的笼子里。在那儿没人会伤害我。
今天天亮后,我起身去饮水,发现了另一个巴纳比。
“你好,”我打着手势,“我也是巴纳比。”
另一个巴纳比朝我低声咆哮。
“你住实验室么?”我问,“你的笼子呢?”
另一个巴纳比朝我猛扑过来,又踢又打。我尖叫着在地上滚成一团。
“我做错什么了?”我问。
另一个巴纳比又对我发起了一轮攻击。我哇哇大叫着爬到了树顶。另一个巴纳比坐在树下死死瞪着我,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开。天很冷,又下起了雨。我一整夜都在瑟瑟发抖。我多么希望这时萨利能来啊。
天亮后,另一个巴纳比没有回来。我爬下树,嗅了嗅它待过的地方,循着它的气味找了过去。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最后,我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巴纳比的数量超乎我的想象。我回忆起萨利教我的计数知识,然后数了起来——总共二十三个巴纳比。
其中一个巴纳比发现了我,尖叫起来。我还没来得及打手势,它们就朝我冲了过来。我转身就跑。它们追了我很久才放弃。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了。
我孤独了很多天。我没有回去找那些巴纳比,因为它们一有机会就会伤害我。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不惹它们生气。
我学会了在大猫离我很远的时候就闻到它们的气味,然后爬上树,以防被它们抓住。我还学会了躲开那些会发出笑声的狗——以前萨利看见我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也会发出同样的笑声。但我还是很孤独。我想念能与萨利交谈的日子。我已经忘掉她教给我的一部分手语了。
昨天晚上,我梦见弗雷德、巴尼和迪诺了。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渗水了。
早上,我听见了异样的声音——不是大猫或者狗发出的那种,而是更加奇特、古怪的声音。我循声而去,想看看是谁发出的。
在一片开阔地上,我看见了四个人——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他们带着一只褐色的笼子。这只笼子没有我以前住过的那种好,因为从外面看不到笼子里面的样子,想必从里面也看不到外面。
有个男人生了堆火,他们围着火,坐在凳子上。我想要靠近他们,但我从跟别的巴纳比的接触中学到了教训,所以我静静地待在一旁,直到有个男人看见了我。
他没有尖叫,也没有追赶我。于是我朝他打了个手势。
“我是巴纳比。”
“它在比画什么呢?”有个女人问。
“没什么。”一个男人答道。
“巴纳比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我继续打手势。
有个女人把什么东西举在自己面前,那东西突然发出“喀嚓”一声。我的视野里瞬间一片白色,什么也看不见。我揉了揉眼,继续走上前去。
“别让它靠得太近!”另一个男人说道,“不知道它有没有携带什么病菌。”
“你们想同巴纳比玩儿吗?”我问。
发现我的那个男人捡起一块石头,朝我扔过来。
“滚!”他大喊道,“快滚开!”
天黑后,他们围坐在火堆旁。我悄悄地溜到离他们尽可能近的地方,躺下来,倾听他们的交谈声。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实验室里。
天亮后,他们又朝我扔石头。我识趣地走开了。
之后又过了很多天,我发现了另一个孤独的巴纳比。它是雌性,身上布满伤痕,都是别的巴纳比留下的。它看见我的时候,龇牙低吼着。我静静地坐在地上,希望它不要离开我。
过了很久,它朝我挪了几步。我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我不想吓到它,或者惹它生气。我装作没看见它似的,直愣愣地盯着树林。
终于,它伸出了手,从我肩上抓起一只昆虫,喂到自己嘴里。很快它就坐到我身边,吃起掉落在地上的花瓣和树叶来。
我确定它不会离开我,于是朝它打了个手势:“我是巴纳比。”
它抓住我的手,以为我正在摆弄什么水果或者昆虫。当她发现我手里空无一物的时候,忍不住朝我龇了龇牙。
它并不比罗杰聪明,但至少它没有离开我。
我决定叫它萨利。
萨利害怕别的巴纳比,所以我们决定住在森林边缘,那里很少有别的巴纳比来。萨利会抚摸我,感觉很舒服,但我愈发怀念能交谈和思考的日子。
我每天都试着教萨利手语,但它就是学不会。我们生了三个小巴纳比,每年雨季后就生一个,但它们的智力水平与萨利差不多。而且,我已经把大部分手语搞忘了。
越来越多的人坐着褐色笼子来森林。萨利和孩子们都怕他们,但我最喜欢交谈、倾听和思考了。我经常晚上去他们的营地,在黑暗中听他们讲话,竭力理解那些字词的意思。我想象自己又回到了实验室,尽管我差不多已经忘记那里是什么样子了。
每当有人发现我,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打手势说:“我是巴纳比。”但没有人看得懂。如果哪天有人回应我,我想那个人肯定是上帝。
我曾经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他,但现在我几乎把那些问题全忘光了。我只想让他好好对待萨利和实验室的另外两个人——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因为我的遭遇并不是他们的错。
我不会问他为什么恨我、把我造得如此特殊,也不会问他为什么森林里的人和其他巴纳比都讨厌我。我只会对他说:“请您跟巴纳比说说话。”然后,我会让他给我上一节课。
很久以前,我是一个聪明的小家伙,有很多问题想同上帝讨论,但我早就脱离了原来的世界,对现在的我来说,能有人跟我说说话就已经足够了。
【责任编辑:明先林】
每日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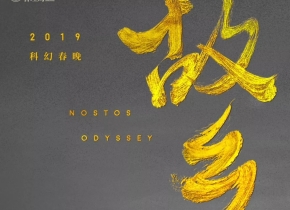
去年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小玲,是在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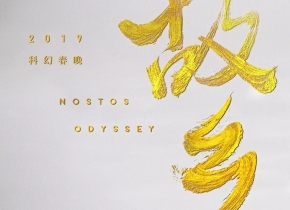
莫名的,在一片沉默之中,我突然接收到......
最热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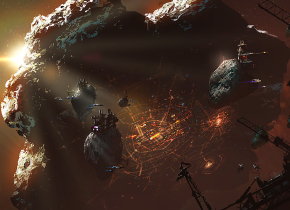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