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首位接受‘换头术’的患者将是一名中国人,地点定在了中国 ,时间是2017年底。”日前,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引爆了国内舆论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由于此前媒体多次报道,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将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手显微外科中心主任任晓平合作, 实施世界首例人类“换头”。因此虽然这次国外媒体报道没有指明实施手术的医生是谁,但媒体还是聚焦到有中国“换头术”第一人之称的任晓平身上。
任晓平“闭关”不接受媒体关于换头术的采访已半年有余,出人意料地是,当本文记者电话联系到任晓平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记者当面采访的要求。除了对于国外媒体报道予以否认外,他还表示,如果意大利专家提出正式邀请,他“乐意帮助他完成此项手术。”
传言篇:
他屡次置身争议旋涡中

处于舆论焦点的任晓平
争议肆起,仿佛一个漩涡刮了好一阵。而身处漩涡中心的任晓平却在回复了一些问题之后消声了一段时间。
1996年,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工作的任晓平,应邀赴世界著名的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克拉纳特手显微外科中心”进行临床研修,师从美国著名手外科专家克拉纳特教授,从事手外科疾病的诊疗及科研工作近五年。
2012年他以特聘教授,外国专家名义引进回母校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
任晓平曾成功地设计和完成了世界首例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的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相关实验研究,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将该成果发表于美国《显微外科》杂志,此设计被誉为世界第一例成功的异体复合组织移植模型。
基于这项研究成果,任晓平教授在“克拉纳特手显微外科中心”参与完成了人类第一例成功的异体手移植(CTA),该病例现已术后成活17年,为国际CTA存活时间最长的成功案例。
尽管这些头衔、经历证明着他的学术背景和水平,但他将参与“换头术”的新闻一出,仍立刻引来一片声讨与质疑。
“先稍等一下”是这位大忙人的标签注脚

任晓平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的合影
“先稍等一下,我先接一个记者电话。”下午两点,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一间办公室,任晓平一边接电话,一边和北京科技报|北科传媒记者打招呼。似乎每一次的媒体关于“换头术”的报道一出,任晓平的工作和生活就会被打乱。
记者细细的观察着这位身处舆论焦点的医生,稀疏的发际、略快的语速,回答记者问题时几乎不假思索;被誉为中国“换头术”第一人,然而任晓平的办公室却同记者之前所见到的其它医生的办公室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一桌一椅,桌子和窗台上摆放了一些书籍,略有翻动的痕迹,手边一沓英文文献的复印件……可能唯一醒目一些的就是背墙上的一排英文证书。
凭着有限的专业英文功底,记者认出其中一些关于外科手术类的,唯一一张中文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对任晓平的聘书。
“院领导这边临时通知三点半有一个会要我参加,可能有点紧急”,任晓平很忙,出门诊、做手术、搞研究、带研究生、参加会议,似乎争议等来自外界的影响并没有过多的搅扰任晓平的正常研究。

或将接受世界第一例头颅移植手术的俄罗斯男子Valery Spiridonov
“我参与换头术的说法很多都是以讹传讹”
谣言、猜测、争议,媒体的报道在卡纳维罗宣布实施换头手术之后接踵而至。
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任晓平表示,手术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仍没有敲定,一些媒体大肆宣扬的内容很多都有待商议,就是“换头术”一词也仍够不准确。
对于公众,可能“换头”一词颇为大胆且神秘,但是任晓平直言,现在通俗的说法是“头移植”或者“换头术”,这沿用了传统的“器官移植”得来的,但这种说法不科学,容易误导人,因为头部并不是一个器官。
“6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给猴子进行头部移植的美国医生罗伯特•怀特认为,应叫‘身体移植’,但这种说法也没有被大家沿用。意大利的卡纳维罗医生将其命名为‘天堂(HEAVEN)手术’,是“头部接合冒险手术”的缩写,但我认为这种叫法不太严谨,缺乏学术性。”
任晓平更倾向于“异体头身重建术”这一命名。“我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参加学术活动时广泛征询临床、基础领域专家的意见,探讨之后提出“异体头身重建术”的命名方法,已经用了几年。这个名字我感觉比较合适,更科学,而且能说得清楚,且降低了手术的敏感性,毕竟“头移植”有时候听起来让人不舒服,而“异体头身重建术”就比较中性”。
不仅“换头术”一词令任晓平颇有微词,卡纳维罗的言辞也显得有些“特立独行”(西方很多人对他的评价),“2017年底,任晓平将与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卡纳维罗共同完成人类第一例换头手术”的消息不胫而走,也另任晓平颇感无奈。
“他若邀请,我必接受”
面对许多“以讹传讹”的消息,任晓平告诉记者,关于手术,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谁来做,都是未知数,卡纳维罗个人比较想将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因为现在针对换头术所存在的争议是有的,他更想用自己的研究和行动去推动这件事情,向着临床的方向进行转换,以此为目的,卡纳维罗的语言就可能比较偏激,任晓平“就事论事”的语气晓得非常平和,至于诸如时间地点等问题,任晓平表示:“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他极力想让这件事在俄罗斯或欧洲完成,时间上仍不确定”。
任晓平还提到,目前卡纳维罗对他的邀请只是“口头上的”,正式的书面邀请还没有,但是任晓平表示,如果卡纳维罗向他发送正式的邀请,他将会接受,“我是乐意帮助他完成此项手术的”。
技术篇:

“脑袋搬家”的技术路径是否可行?
可能很多人听到换头除了大吃一惊之外一定会提出一个疑问:换头到底能不能成功?在安全性上究竟能否保障志愿者的生命体态呢?
任晓平告诉记者,第一例异体头身重建在未进行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从目前现代医学的发展程度来看,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实验都是从动物开始,进而在人类得到临床应用的,此次人类异体头身重建术也不例外。
根据卡纳维罗在《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描述“异体头身重建术”的论文显示,“异体头身重建术”主要有一下几个步骤:首先,必须要对接受头部移植手术的病人和捐赠人进行降温处理,进而放慢细胞死亡的速度;切下他们的头,并将主要的血管连到事先准备好的管子上;最后,切断脊髓,并尽可能保证伤口的清洁度。而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如何融合脊髓及内部神经成为了关键。
卡纳维罗打算用聚乙二醇解决脊髓连接融合问题。之后就是血管、肌肉和皮肤的缝合。卡纳维罗表示,术后病人的昏迷情况将可能会持续好几周的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医生会用电极刺激病人的脊柱,进而加强其与新神经的连接。如果病人体内出现排斥情况,医生则会向其体内注射抗排斥免疫抑制剂。卡纳维罗表示,如果手术成功,那么结合物理疗法,病人可在一年之内恢复行走能力。
“这个顺序是对的,应该考虑或者说这是环节中一个很好的设计,但这个设计方案能不能经得起实践检验,需要在实验中来完善它、验证它。如果这套方案不行,我们要采取相应其他方案,我们要准备好备用方案。目前报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任晓平说。
4分钟,是接上头部和躯体神经的最长时限

同时,任晓平也提出了“异体头身重建术”需要克服的难点。
首先是缺血器官的损伤,传统的器官移植我们都会在有效的时间内尽快接上,心脏、肾脏等器官如果保存好了,几个小时内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手部两三天都有存活的。“但是头部不行,太复杂!不仅是存活问题,患者的智商必须得以保证。”但头部在室温情况下超过4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通血之后,很可能脑细胞已经坏死,这样就相当于手术失败。目前全世界还没对这一方面进行足够重视,很多非专业人士会把它简单化,一带而过。其实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第二个难点是免疫排斥反应的问题。因为异体头身重建的特殊性,其中涉及复合组织的重建和中枢神经功能的保护,在重建之前我们必须回答和解决脑中枢神经是否是一个免疫特赦区,是否能够被目前的复合组织免疫治疗药物有效控制,选用何种方法抗排斥效果会更好,术后又如何有效监护和评价这一特殊“器官”,这些仍需在实验中寻求结果。
第三点就是中枢神经的连接和修复,这可能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和争议。
中枢神经是“活”下来的重中之重
用任晓平的话讲,中枢神经的连接和修复非常困难,“因为对头部中枢神经来说,不确定因素太多”。
任晓平作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显微外科中心主任,在外科领域一直走在前沿。“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国外,那时国际医学界在挑战复合组织移植,‘头部移植’是复合组织移植的最前沿,而我们要攻克的第一个复合组织就是手部。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我们启动了这一研究,花两年时间才完成临床前的实验,完成人类第一个手部移植手术,到现在也是存活时间最长的移植手。攻克手部移植后,面部移植自然就突破了,因为解决了免疫药物学方面的难题,这方面一突破,整个领域就带活了。现在,全世界各身体复合组织的移植零零散散已有200例左右。”
做完手部和面部移植后,任晓平的下一步挑战自然就会想到头,“不过这个想法并不新,无论从民间传说还是此前的科学界,都进行过探索和尝试,只不过上个世纪这项研究只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要用现代技术来认真从事这项研究”。
不同于手、面部等部位,头部移植在此基础上的要求更高,而中枢神经的连接则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
国际神经修复学会创始主席黄红云曾表示,头移植术最核心的难点是延髓和脊髓的解剖结构和功能性连接。换头术相当于颅颈交界区脊髓完全横断性损伤,而完全横断性脊髓损伤后,损伤段以下神经功能丧失的直接原因,是上下行传导束的轴突传导功能连接中断。对于高等(如人类)哺乳动物,切断后的轴突也许可以做到瘢痕组织物理连接,但靠黏合剂是无法让已损伤的上下端轴突结构连接,并恢复功能。这是因为:轴突一旦被切断后即刻形成溃退,而轴突的重新连接是轴突再生的过程。
对此,任晓平表示,“中枢难不难?难!重不重要?重要!但我要将它放到最后一位,因为它涉及术后身体有没有良好的功能,就好像如果患者生存,但却没有智商、不能良好的行动,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是手术的目的。我曾经表示,这个项目要分步走,第一步要有效解决缺血和免疫排斥问题,那么病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就能挽救他的生命,让他有良好的思维,这就算是个阶段性的成果。有了第一步的基础,第二步才是功能恢复,让接受手术者有一个生活质量。传统医学认为中枢神经不能恢复,但近十年的医学不断发展,这个结论几乎要被推翻,不论科学研究还是临床,都有很好的实例。这个项目很有希望,但这个希望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科研基础上,项目所需的人力物力非常大,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伦理篇:

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
争议:手术风险大,不成功就是“谋杀”
任晓平:不做永远都不可能成功
异体头身重建仍有很多实际问题有待实验,从而在临床实施上拿到更大的把握,这是横在将要参与到此次异体头身重建手术的人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困难。
然而,“换头”消息一经披露,却受到了很多争议,甚至演变到了一片口诛笔伐的状态。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专家王长希教授对所谓的“换头术”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从技术上不可行,“这是无稽之谈,百分之百失败的手术,以后肯定是个笑话。这样的手术太超前,没有可能成功。而且,即使接受手术的病患本身同意,也涉及谋杀,在伦理上更加不可能。”王长希说。
“我觉得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评价‘换头术’只是艺术家的想法,同种异体脊髓的功能重建和再生,复杂的伦理问题将是两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瑞典留学归国的器官移植医生、厦门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齐忠权如是评价,“目前没有科学数据支持脊髓再植可以成功,更何况异体移植。如果耗费巨资把目前所谓换头‘适应症’患者治疗成一个高位截瘫或近乎高位截瘫者,且需要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医学界的同行不会达成共识。”
“这是不是一个愚人节玩笑?”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伦理学家翟晓梅听到此事的第一反应,“要不就是在炒作。”在她看来,这一手术风险很大,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翟晓梅认为,如果手术是为获取科学知识,那是为了将知识应用在其他人身上,这时就必须做利益风险评估。如果是为了在临床上解决患者的问题而采取创新性疗法,翟晓梅说,那也需要提供“有道理的方法”,“不是科学家自己说有道理就行了,必须是医学共同体公认的道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则把这件事情称作“人体的登月工程”。头和躯体结合之后,还是不是头来主宰整个人说不清楚。“美国有科学家称细胞是有记忆的,如果细胞有记忆,躯体会有独特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和大脑是不匹配的。此时,他的大脑和身体就会出现矛盾。”
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神经外科教授戈德史密斯则表示,这个换头计划规模太大,潜在问题极多,非常难实行。美国神经外科协会专家巴杰则直抒胸臆:“我不希望任何人做这种手术,这比原样儿病死还糟糕!”
面对一片声讨,记者在任晓平的眼中看见的是一份坚韧,态度也显得非常笃定,“技术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果不做,那么永远都不可能成功,我们一直尝试着不同的方式去将各部分进行完善,从事这方面研究,就是为了让技术达到最佳”。
任晓平用世界首例心脏移植举例,“心脏移植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但是现在仍未完善”,1968年1月9日,南非医生克里斯琴-巴纳德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然而患者仅生存了两周,“但是正因为巴纳德医生的举动,才开启了人类器官移植的大门,没有当时的两周,就没有随后的两个月、两年,甚至是二十年”。中国医师协会曾发表文章表示,在医学史上,巴纳德医生的举动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它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所起到的社会意义也许比它在医学上的意义还要重要,它使所有器官移植手术都成为了可能。
争议:“换头”后,如何区分头和身体的归属?
任晓平:人的生命才是至高无上的
从本质上来,异体头身重建或将成为人类医学发展的里程碑,手术将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对参与人员、或者说医学技术水平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然而技术难题可能并不是摆在手术面前的最大障碍,医学伦理上的争议或许才是另研究人员最头疼的。
记者曾就基因编辑人类胚胎问题向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发出过采访邀请,后者因为首次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以探索治疗地中海贫血症的新途径而获得《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人物,但是黄军就却以“想要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邀请,这或许只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军就的研究工作不仅收获了奖项,也将一片“伦理声讨”收获囊中。
而此次的人类“换头”同样被套上了伦理枷锁。
“头接上后,如何去区分头和身体的归属,临床上没有这样的案例”齐忠权说,换头或者换躯干,无论从患者心理还是医学和伦理学方面,都是难以接受的。“意大利出了很多艺术家,但我们是科学家。”
齐忠权所提出的伦理争议并不是一家之言,“换头”消息的披露不仅引发了技术争议,在伦理方面的声讨也喧嚣尘上,诸如“换头之后究竟是‘谁’”、“如果对身体不满意,是不是还将再换”等问题不断浮现,甚至不乏一些宗教人士将科学研究与教义、神话相连。
面对伦理争议,任晓平回答得非常直接,他提供给记者很多英文的文献,“这些很多都是国内外的专家撰文,从伦理的角度阐述人类换头的文章,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多关于伦理的内容”。他告诉记者,从伦理学方面的探讨是必要的,无论是对于公众还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但从推动人类医学技术的发展角度来讲,新生事物如果你不做,问题永远回答不完,只有你去实际的进行尝试,那么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任晓平认为,在做之前,科学家、研究人员、媒体等各方面具有引导的责任,但是这样的引导作用毕竟有限,只有将实际的结果拿出来,才能说明一切。就好像百年前爱因斯坦对于引力波的预言,百年后人们才用LIGO证明其真的存在,但是在LIGO建设之初真的能够确信能够观测到引力波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争议:伦理学阻碍科学发展
任晓平:面对病人的生命,伦理学必须要让步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质疑、争论变为实际的过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这样,一切都准备就绪,再进行实际的操作,得到一个百分百确切的答案,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每个科学进步都伴随着一定的质疑和争论发展而来,倘若你不做,这项科学就会停止”任晓平告诉记者,头部移植被学界束之高阁已经近半个世纪,早在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怀特博士及其助手就首次为灵长类动物恒河猴施行了换头手术,接受手术的恒河猴存活了8天,不仅存有意识,而且可以吃东西,眼睛还可以跟随人在室内的走动。
“怀特做了一辈子的科学研究,但是由于伦理问题以及社会的一些偏见、宗教的阻碍,最后使得科研停滞”任晓平回忆这位在他眼中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时无不惋惜。
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医学在技术上要比怀特时代发达许多,但是当时怀特面临的伦理等阻碍却仍然存在,今天头部移植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如果再阻碍,可能十年、百年之后,这仍将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
任晓平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伦理学是个行为规范科学,面对病人的生命,伦理学必须要让步。如果一个技术可以有效延长人的生命,伦理学角度没有理由不批准。对于新事物,伦理学可以制定一个规范,让新技术在这个框架以内进行,但没有道理阻碍科学的发展。“我认为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个基础上,伦理学的一些规范可以帮助临床实践”。
怀特曾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开篇写道:“在人类器官移植领域,人们取得了很快的进步,从肝、肺、心脏、肾到最近双手的移植都成为了现实,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一件以前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移植人类的大脑。”怀特预言,移植大脑将在21世纪初期成为事实,“那么我们是否作好了移植头颅的准备呢?一些技术条件的确业已存在。”
诚然,怀特的预言在时间上似乎非常准确,但是其所面临的阻碍却随预言一样绵延至今。
TIPS1: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们
肾脏:人类首次移植的器官是肾脏。1954年,美国外科医生Joseph E. Murray对一对双胞胎实施肾脏移植手术。Joseph E. Murray也因在“人体器官和细胞移植研究”的贡献而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心脏:1968年1月9日南非医生Christian Barnard在开普敦的一家医院里成功地进行了有史以来人类首次心脏移植手术。受术患者华什坎斯基受用了一颗在车祸中丧生的25岁的妇女的心脏,最后仅生存了18天。
肝脏:世界上第一例肝移植是由肝移植之父、美国的Thomas Starzl教授于1963年完成。而第一例活体肝移植则是在整整25年之后,即1988年12月8日巴西圣保罗医科大学的Raia医生完成。患者为一位4岁半的女童,供体为患儿23岁的母亲,术后因出现严重的溶血反应,于术后第6日死于肾功能衰竭。
胰腺:1966年12月16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外科等单位完成了世界首例胰腺移植。
骨髓:1956年,美国医生Edward Donnall Thomas为一名白血病患者成功进行了世界上首例骨髓移植,1990年,他与世界首次完成肾移植手术的Joseph E. Murray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肺:1963年,Hardy等实施了人类第一例左侧单肺移植术,患者仅存活18天。
TIPS2:第一个“换头”志愿者:瓦勒里·斯皮里多诺夫
第一位自愿接受全球首例“换头手术”的志愿者名为瓦勒里·斯皮里多诺夫(Valery Spiridonov),已经年满30岁的斯皮里多诺夫是以为俄罗斯的计算机工程师,他患有Werdnig-Hoffmann病,也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这种疾病会导致患者的肌肉停止发展、退化,这令他自小全身伤残,骨骼畸形,而脊髓性肌萎缩目前尚无治疗方法。
斯皮里多诺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表示:“我对科技很感兴趣,对任何能够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进步也很感兴趣,无论结果如何,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还能为子孙后代奠定一个科学基础。”他相信,这台手术将帮助他延长生命,同时也将给科学研究带来巨大的福音。
第一个“换头”发起人:赛吉尔·卡纳维罗
赛吉尔·卡纳维罗,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2015年4月,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宣布将在两年内完成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引发外界关注。
卡纳维罗首先于2015年2月,在《国际外科神经学》期刊刊登了一篇综述目前脑移植技术的文章,称现在技术已可以实现“换头”。随后在4月宣布“换头术”将要实施的消息,并选定了志愿者——俄罗斯工程师斯皮里多诺夫,以为因脊髓性肌萎缩而无法行动的患者。
文/记者:吕浩然 图文编辑:陈永杰 (北京科技报/北科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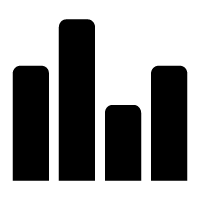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