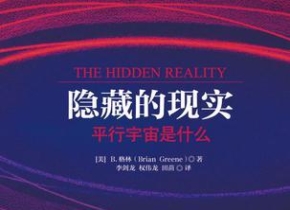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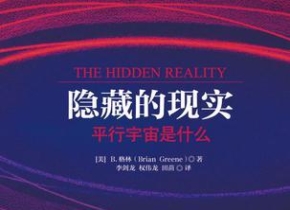

来自: 洛之秋 (Chinga tu madre)
Slaughter House Five的评论
小小的诺曼底在2004年的6月,终于有了久违的热闹。六十年前的“霸王行动”(Overlord)成了美英法三巨头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伊拉克战争而破损的美法友谊似乎也随着在诺曼底的一席叙旧而重新升温。德国总理也来了。他说德国应该承担战争的责任。德国人一向善于忏悔,自从前总理几十年前面对犹太人坟冢的惊世一跪,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赢回世人的尊敬。斯皮尔伯格也来了,他和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一起席地而坐,讨论《拯救大兵雷恩》是不是恰如其分的刻画出了奥马哈海滩的惨烈。
有人说,当年奥马哈海滩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死去的,一种是将要死去的。这样的话自然是夸张了些。虽然盟军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光奥马哈一天就战死了两千五百人,但是毕竟幸存者还是多数。老兵六十年后故地重游不知道该是什么心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点:一,庆典的重头戏跳伞表演将由年轻的小伙子来完成;二,七十年的庆典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等不到。他们能幸运的从德国军队的弹幕中逃脱从而加入到进军巴黎、进军柏林的行列,但是他们谁都没有逃脱时间之幕的幸运。
而诺曼底战役,已经俨然成了战争机器的加冕表演。战争与邪恶的简单二元对立中,诺曼底成了盟军这个正义之师的梦想剧场。他们登陆,他们解放,他们杀人,他们被杀,他们退伍,他们老去,他们回忆,他们老死……
然而还有谁会记得Dresden呢?我敢打赌,明年纪念(或者质疑)Dresden轰炸的声音会被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种种庆典吞噬的一塌糊涂。
垂垂老矣的Vonnegut到时候又会想些什么呢?
幸好Vonnegut作为Dresden轰炸的亲历者,在1969年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叫做Slaughterhouse Five的小说。
这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反战小说。有人称之为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它的最终文学地位还有待时间来确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主人公Billy Pilgrim在时空中穿梭往复的科幻因素丝毫没有减损这部书的现实意义。和Billy一样,Vonnegut是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德国人的阶下囚,被关押在Dresden的监狱。
Dresden是德国中东部的一个历史名城,这里是德意志民族工业与文化中心。这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军事目标,这里有的只是像茨威格博物馆一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密集的居民住宅区,还有随着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而逃亡到此的几十万难民。这个城市也是为数极少的几个在开战后尚未被轰炸机光临的地区,纳粹部队甚至自信得没有在这里布置起码的防空炮火。
而手无寸铁的Dresden,终于还是成为了盟军轰炸机的屠宰场。
这一系列作战计划的出笼,来自一位叫做Charles Portal的英国人在1941年发表的军事主张:通过有选择的将某些城市夷为平地,盟军可以最有效地瓦解德国人的作战士气。1945年2月,在战争结束的前夜,Arthur Harris在征求了美英首脑的同意之后,决定使用这种战术来将Dresden从地图上抹去。
面对轰炸的惨烈,任何人类的语言恐怕都显得苍白无力。盟军为了达到摧毁城市的目的,大量使用了燃烧弹作为武器。这种武器的物理化学原理是通过投掷积簇式可燃炸弹,点燃弹壳中有的镁、磷和凝固汽油。被轰炸目标起火燃烧后,投弹区域空气温度急剧上升并变得异常稀薄,没有被烧死的也会因为缺氧而死亡,而区域外的冷空气从底部窜入补充,气流速度之快足以将外围的逃难者卷起抛入爆炸燃烧区,然后将之杀死。
这种构思新颖的杀人方式在1945年的2月13日得以完美实施,英国皇家空军的773架兰卡斯特号飞机奉命起飞,让夜幕下的Dresden顿时成为了地狱般的火海。而在这其后的两天,美国空军的527架重型轰炸机接踵而来,终于用燃烧弹将Dresden彻底摧毁。死亡人数的统计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很多外地难民的身份都已经付之阙如。最保守的估计是35,000人遇难,而最新的研究则显示很可能实际死亡人数在10万到15万之间。
也许历史书对于二战的正邪评判已经有了公论。Dresden的惨剧最多让人惋惜一下战争的残酷,然后会反过来将这一切罪孽推到希特勒的头上。“谁让德国先开的第一枪呢?”这是我们通常面对盟军在德国的杀戮所能找到的托辞。
英国皇家空军司令Robert Saunby在战后谈到Dresden轰炸时说:“谁也不能否认Dresden轰炸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不是这些或者别的什么战争方式让这一切变得不道义和不人道。真正不道德的是战争本身。一旦战役全面打响,它就不能被人性化或者文明化。如果一方尝试这么去做,那么它就最可能被打败。对于我来说,这就是Dresden的教训。”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这么样的呢?Dresden轰炸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呢?
如果从单纯二战战局的发展来看,这次轰炸不仅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甚至是极其多余的。在1945年的2月,德国的败势已成为定局,盟军的全面胜利只有几个星期之遥。Dresden没有任何的军事要塞或者与军事有关的重要设施。摧毁Dresden不能对纳粹的战争机器带来任何的实质性打击,既不能加速也不能减慢最后胜利的到来。
但如果从二战后期美英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博弈来看,Dresden的命运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邱吉尔和罗斯福都清楚的了解,英美联盟的战略除了推翻希特勒的纳粹统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企图就是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苏联红军的势如破竹让邱吉尔开始担心Dresden当时很快就会被苏联人接管。为了让共产主义者吃不到这个到口的肥肉,美英决定将这个德国第七大城市炸掉。用几万条血淋淋的生命代价来削弱苏联在战争中的强势地位。一份英国皇家空军的内部备忘录甚至就赤裸裸的公开表示:“攻击的目的是….顺便可以让俄国人抵达的时候知道我们轰炸机的厉害。”
David Pedlow在2004年2月14日写给英国《卫报》的信中,转述了他当年参加过Dresden空袭的父亲的回忆。他父亲当时登上飞机发现这次的任务和以往的都不一样。以前的作战飞行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轰炸目标,而这次指挥部没有作任何规定,只是告诉他们看到有密集建筑物的地方投弹即可。显然,这次大空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戮平民,制造恐怖。到最后,甚至连火海上空的盟军飞行员都在为这些德国老百姓的可怖处境担心。
Vonnegut作为美国战俘,在Dresden的Slaughterhouse Five里见证了自己战友的这次杰作。他是该欢呼还是诅咒呢?当他数月后被苏联红军解救回到美国,他已经失去了讴歌这次战争的勇气。他笔下的Billy毫无生气,毫无斗志,毫无思想,用他的话说活脱脱就是一个可口可乐罐。他说他的书中不存在戏剧性的人物(character),因为战争阻止了他书中的一切character成为character。他说战争开始时,奔赴前线的都是男孩(boy),而侥幸活着回来的则都变成了男人(man)。而这,都要归因于战争。
让我们对Dresden触目惊心的除了那累累的焦尸,更多的其实是“正义”一方的邪恶本质。即使是纳粹法西斯在欧洲攻城掠地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以摧毁市民生命为核心使命的战争方式。而这一切,都被诺曼底的登陆者以自由为名行之,而且讳莫如深。
德国人已经在一切可能或者不可能的场合为他们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而忏悔,而访问Dresden的英国女王却从未对那里的无辜亡灵表示过一丝一毫的自责。德高望重的英国主教George Bell在上院痛斥Dresden轰炸为战争罪,而更多的英美主流社会人物却在保持着沉默。
今天是纪念对法西斯作战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日子。写下一点零碎的文字。只是为了告诫世人,只要我们一日对自己的邪恶不敢加以正视,法西斯的阴魂就一日不会随着德国战败投降而散去。
写于2005年5月14日
转自:http://book.douban.com/review/1580755/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科普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其它相关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最热文章

对于100年前甚至只是50年前的人来说,今天的城市看起来已经完完全全是一副未来都市的样子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n

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流逝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银翼杀手》\n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