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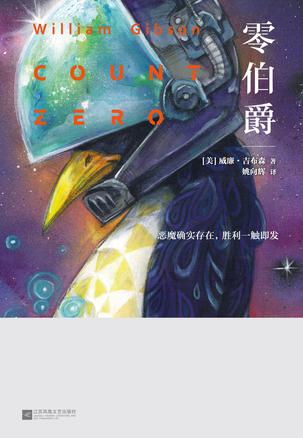
来自: 往时瀚默
零伯爵的评论
自从1984年威廉•吉布森发表了《神经漫游者》之后,赛博朋克从一个科幻类的亚文化种、不上台面的小说流派,发展到影响影视、动漫、游戏甚至黑客等领域的文学现象。呈现在你眼前的这本《零伯爵》,其声誉虽不如《神经漫游者》,但继承了作者代表作一贯以来后现代主义特质,以玛斯和保坂两家巨人企业的割据竞争,描绘了一群后现代科技世界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引发出对新科技的发展可能给社会及人类自身带来的种种影响。在威廉•吉布森的蔓生都会三部曲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阴郁冰冷的末日色调
《零伯爵》后现代主义特质的第一个表现是阴郁冰冷的末日色调。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银翼杀手》最后仿真人有一段令人记忆犹新的台词:“我曾见证你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事物。在猎户座的侧翼,攻击星船灼灼燃烧,在唐豪塞星门旁,我看见C射线在黑暗里熠熠生光。那所有的瞬间,都将湮没于时间的洪流,就像泪水消逝在雨中。”这段台词仿佛预言一般,揭露了人类社会那个宏伟而又凄凉的“未来”。威廉•吉布森深受《银翼杀手》的影响,他笔下的未来世界阴暗而奇特,以《零伯爵》为例,书中的世界就像一座发展过度、肮脏混乱、阴雨不断、带有哥特风格的巨型垃圾场。如书中的“台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烛泪和酒渍。奇形怪状的印记彼此交叠汇成黑漆漆的一片,还有几百个烟头留下的深色烫痕”、“歪七扭八的过道从咖啡小亭前方的区域向外延伸,煤油灯嘶嘶喷出白色火苗……东芝监察机器人呜呜驶过走廊,拖着伤痕累累的塑料推车”这类的描写数不胜数。作者这种笔调可谓黑色狂想与复古气质的完美混搭,夹杂了新浪潮诗意现实主义的感伤气质。书中那些泛滥的物质、破旧潮湿的建筑、色泽诡异的灯光、雾气阴冷的街道、无精打采僵尸一般的人流,一起构筑了抑郁、绝望而又奇妙的末日世界。作者着力绘制的这一座座冷色调缔造的城市森林,为我们呈现出后现代那片光怪陆离的荒原,反映了其对物质过度发展、未来科技世界的忧虑反思和深沉拷问。
二、反英雄和边缘人
《零伯爵》后现代主义特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作品里面描绘的这群类似“反英雄”、“边缘人”的人物。这些人物颓废而真实,塑造得富有时代意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近乎社会弃儿,仿佛卡夫卡在小说三部曲当中遗留的血脉。他们自甘堕落,出没于下三滥的酒吧和阴森潮湿的小巷中,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猜忌、仇恨与背叛。作品中,雇佣兵特纳是一名企业黑客,刚刚被一场大爆炸炸得粉身碎骨,转眼之间又被拼凑而成,保坂公司雇用了他,给了他全新的身体和生物芯片,去帮助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米切尔携带他的发明——一种蕴藏巨大潜能的生物芯片从玛斯出走投靠保坂,特纳在这场网络空间战争身负诅咒和悬赏,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展开行动。波比是一名业余黑客,他一直想在“赛博空间”出人头地。一个犯罪团伙给了他一个黑市软件“破冰者”,当他利用软件插入头部企图进入“矩阵”的时候几乎丧命,在弥留之际脑海里一个女孩的印象挽救了他,这次事件引起了他对最近发生的类似事情的研究。玛丽是巴黎一个小画馆的老板,她被一个巨富、艺术赞助人约瑟夫•维瑞克诱惑去卖掉一件伪造品。他们都被动地卷入了巨型企业恶斗的各种阴谋和冲突中,而且已被人工智能神秘地控制了。和“传统”的科幻作品那些为了称霸世界而使用科技的野心家不同,《零伯爵》中的主人公都是在“高科技”背景下,在人工智能的监视下,在社会的夹缝里,战战兢兢维持着“低生活”标准的可怜虫。他们的特征以原文当中一段描写最佳:“他的宽脸很白,尸体般的白。他的眼睛有黑眼圈,眼窝深陷,漂白的乱发向后梳”。虚弱无力的他们,甚至连完整的人类都算不上,在科技为王、道德真空、黑暗可怖的时代徘徊,连希绪弗斯式的抵抗都无力做出,只能随波逐流,选择“冷漠”和“放弃”。这无疑是威廉•吉布森对现代社会、仿真威胁和人性遗失的当头棒喝,令人掩卷而思。
三、碎片化的叙事特征
《零伯爵》后现代主义特质的第三个表现是作品里碎片化的叙事特征。碎片化的叙事特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现实和虚拟的不停切换,一个是叙事视角的不停切换。哲学家迈克尔•海姆认为:“赛博空间暗示着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维度,在这里我们把信息移来移去,我们围绕着数据寻找出路。” 在赛博朋克文学中,大多故事发生在网络上、数码空间中。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界线很模糊,经常使用人脑和电脑的直接连接,所以被称为“数字科幻”。《零伯爵》完美地呈现出“数字科幻”的感觉,其节奏飞快,信息量密集,经常像电影镜头一样迅速切换,同时大量使用俚语、无头无尾的短句,现实和幻境随着表述不断转换。如玛丽在“矩阵”中会见维瑞克之后,“夜色如翅,扫过巴塞罗那的天空,像是巨大的快速按门一闪,维瑞克和桂尔公园都消失了,她发现了自己回到了皮革矮凳上”。特纳“滑进梦境的浅层海洋,图像飞转,米切尔档案的片段混合他自己的人生点滴。他和米切尔驾驶公共汽车穿过如瀑布般洒落的玻璃渣,冲进马拉喀什那家饭店的大堂。”这种现实和梦境的转化非常具有镜头感,精彩纷呈。另外,转换还体现在叙事视角的变动上,比如以下这段描写,启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这样巧妙的结构:“骨头、金色线路板、死去的缎带、白色的陶土圆球。玛丽摇摇头。一个人怎么能只是简单排列这些零碎、这些垃圾,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抓住你的心灵,像鱼钩似的潜入你的灵魂?但她随即点点头。”完全成熟、切换自如的叙事视角,展现了主人公有限的视角、复杂的情绪以及作者批判的态度。这两种碎片化的叙事特征,组合建构了一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世界。
《零伯爵》的世界里,各国政府已经式微,庞大的跨国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人类生活每一个细节都受计算机网络控制的暗黑地带,作品充斥着强烈的反乌托邦和悲观主义色彩,反映了威廉•吉布森对于大企业、政府腐败及社会疏离现象的担忧。而书中一些预言已经变成现实:躲在房间的新一代社会人,在电脑网络的集合文化下浸淫成长;电视里充斥着雷同的娱乐节目,让无暇思考的现代人进一步麻木;在熙熙攘攘的地铁里,人们都凝视着掌中的手机或平板屏幕,手指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他们的下一代,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会用手指划开智能屏幕解锁,五彩斑斓的仿真世界让他们的双眼失去了童真;而远在天边的组装这些手机的巨型车间里,工人就像机器般永不停息,只有死去才能暂时中断流水作业。毫无疑问,威廉•吉布森所担忧的现代科技及传媒,已经在喧哗与骚动中绽开了一朵朵妖艳的恶之花。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在书中看到了当代科技发展为背景下的人类生存状况;有人看到了带有朋克式反文化色彩;有人还在玩味书与《黑客帝国》视觉呈现的异曲同工。伴随着后现代读者们的“按图索骥”,后现代的《零伯爵》将走出高阁,步入我们的精神世界。
每日荐书

去年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小玲,是在我导......

莫名的,在一片沉默之中,我突然接收到......
最热文章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德国概念设计师Paul Siedler的场景创作,宏大气派。

《静音》是一部 Netflix 电影。尽管 Netflix 过去一年在原创电影上的表现并不如预期,但是《静音》仍让人颇为期待

最近,美国最大的经济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全美超过一半的诺奖经济学得主都曾是该机构的成员)发布了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 1990 到 2007 年的劳动力市场情况。\n

J·J·艾布拉姆斯显然有很多科洛弗电影在他那神秘的盒子里。\n

我们都知道,到处都在重启;我们也知道,如果有钱,啥都能重启。所以,会不会被重启算不上是个问题,只能问什么时候会被重启。自然而然地,世界各地的各种重启现象衍生出了一个有趣的猜猜游戏:哪一部老作品会是下一个接受这种待遇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