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Pixabay
没人知道穆特来·萨扬(Mutlay Sayan)具体的出生日期。他的母亲告诉他那是在夏季的某天,庄稼收割之前。分娩的地点是在自家门廊,邻居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她们用加热过的厨房刀割断了脐带,那年可能是1987年,也可能不是。最终,为了满足官方文件的要求,有人给他创造了出生日期,就像日后萨扬填补自己的各种空白一样。这是个现实生活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从在父母的田地上撒野的小孩子,到伊斯坦布尔棉花加工厂的童工,最后成为美国新泽西州的放射肿瘤专家。(*译者注: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全书描写了童年丧父的主人公成长的故事,是作者带有半自传性色彩的小说。)
萨扬在土耳其最东部长大,那片地区的形状就像鼻子一样,插在亚美尼亚和伊朗之间,每当描述自己童年的时候,他常常以那里没有的事物开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他从没见过汽车或者电视机;他没有上过学,所以不知道周末是什么;他也从未学过阅读。这些回忆对他来说恍如昨日,温暖又鲜活,但也充满了被时光扭曲的奇异感。“感觉就像几个世纪之前一样。”他如此描述道。

图片来源:Pixabay
他喜欢在大清早第一道曙光出现之前驾着马车在田野上奔驰。他记得自己当时个头还很小,父母从棉花蕾铃中摘下一簇簇棉花时,棉花枝长得比他还高。他们还从土壤中刨出甜菜根,等着一辆车路过把它们收走,送去别处制成糖。到收获季节的尾声,一家人会坐在地上,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棉花,大家动手摘除棉花种子。这些种子看上去像杏仁核,剩下没有被送去榨油的种子会被用作冬天取暖的燃料。
对他的同事来说,这种形象很难和他们现在见到的萨扬联系起来:穿衬衫打领带,外面披着一件实验室白大褂,向刚刚确诊的癌症患者详细讲述治疗方案。疗法可能涉及打断肿瘤的DNA链,而用来发射能量轰击肿瘤的设备巨大无比,必须要用吊车吊起,下放入医院内,然后重新盖好房顶。
“我心目中的他使用着我们的质子机器,一台价值1000万美元的粒子加速器,如巨兽一般,他用那台机器来精准治疗儿童的脑部肿瘤。”约瑟夫·维纳(Joseph Weiner)说,他是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癌症研究所临床放射肿瘤科住院部主任,而萨扬目前是这里的首席住院医师。“但这个人在十几岁之前从来没见过灯泡,这听上去很好笑。”
这两种形象是如此不协调,当萨扬第一次告诉维纳自己从哪里来的时候,维纳甚至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他们当时坐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夫拉特布什区克拉克森大道上一家狭小的披萨店内,距离医院不远,那时的维纳还只是住院医师,而萨扬是正在轮转实习的医学生。“我一时都接不上话。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维纳说,“我觉得这一切听上去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虽然在他俩交谈的时候,萨扬给维纳看了自己指关节上的伤痕,那是工厂岁月给他留下的。当时维纳还看不出来,但萨扬自己人生故事的痕迹也能够从他的研究中窥见。他不仅追踪幸存者的统计数据和副作用,还包括潜伏在这些背后的个人经历:远离家庭进行治疗的日子,错过的治疗预约,以及癌症患者的疲劳乏力症状。
“如果你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应该让他活得更好。”萨扬说道,他最近获得了美国生物医药媒体STAT颁发的STAT Wunderkind荣誉。“如果说我们将会延长你三个月的生命,但那三个月会一团糟,那可不行。”
让萨扬走入工厂的正是家中的癌症病人,虽然一开始癌症并没有显露真面貌。“有一年,我的父亲失声了,从此再也没恢复过来。”萨扬说道。他的父亲一直等到收割季结束,才搭车去了离家最近的城市伊格迪尔,那里的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有什么东西正在生长。随后,父亲搭车返回农场,一家人着手卖掉仅有的一点儿土地,举家搬到伊斯坦布尔治疗癌症。
一家人坐了将近24小时的公交车。萨扬记得当时自己11岁左右,有关旅途的一切新鲜又奇异。他记得第一次穿过隧道,告诉母亲公交车正开进马厩。他记得第一次看到电视机,认为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的人也能看到他。他的母亲也有同样的反应,于是立刻用头巾遮住了自己的头发。
他们在巴格西勒安顿下来,那是位于博斯伯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工业郊区。萨扬的父亲开始接受治疗,萨扬和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也都开始在一家纺织厂工作。工作很辛苦,周围尽是震耳欲聋的纺织机。有人会在T恤上缝好一道接缝,然后扔到篮筐里。而萨扬的工作就是收集堆起来的衣服,剪断连在一起的线,叠好带给下一位工人。因为当时他还太矮小,够不着篮筐内部,他不得不跳起来把身子探进去,用肚子抵着篮筐以保持平衡。“你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萨扬回忆说,“你必须在各种机器之间跑来跑去。”
萨扬憎恨工厂。他花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用剪刀剪线头,最后剪刀柄磨破了他的皮肤,开始流血。
然而城市生活很昂贵。他们从农场带来了晒干的玉米棒子,一开始,这些玉米就是他们的所有。医生要求他们给萨扬的父亲称体重,确保他没有日益消瘦,而体重秤成了另一收入来源:每逢周日,萨扬会休息一天,他就带上秤去市场,靠给人称体重挣钱。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就挣到了足够买一些胡萝卜和苹果的钱,当时他心里一下涌出了胜利感。
生活好像在嘲弄他。从工厂的午餐厅望出去,就能看到一所学校,所以他总能瞥见自己不曾有过的生活。他不确定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个念头,总之有一次午休的时候,他来到学校,要求见一下校长。见面之后,他乞求校长能准许他入学。
“她说她很忙,没时间跟我说话,把我赶了出去。”萨扬回忆说,“但她没说不可以。”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他每天都来。他的策略相当简单,就是让校长不要忘记他。“每天扒着窗户和门缝,露出我的脸。”这是他自己的说法。
最终,校长投降了。“我每个月挣11个土耳其里拉,而这位校长,愿上帝一直保佑她,她跟我说:‘好吧,穆特来,我们找到了一份奖学金,可以支付你在工厂所挣的钱,这样你父亲能够继续治疗。’”萨扬说。
一开始,她不知道怎么教萨扬。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不适合待在一年级,但又跟不上六年级的课。所以校长想出了折中办法。早上萨扬跟着同龄的同学上课,而下午图书管理员会教他所缺失的一切知识。“我很害怕,如果我表现不好,他们就会送我回工厂。”萨扬说,“这反而给了我动力。”
三年后他小学毕业,立刻进入了职业高中,学习农业商业。作为家里唯一能读会写的人,他和他的父亲一起预约医生问诊,倾听医生的分析。这点燃了他对医学的兴趣。但让他得以追求医学的是个简直不可能发生的成就和机遇。
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他的GPA在班级里排名第一,从而得到了去美国实习的机会。他在佛蒙特州一户土耳其裔人家里住了一个月。在那期间,他正好看到寄宿家庭的一位姐姐坐在厨房桌边,着手申请大学,她想要学习工程学。
“我当时笑了,跟她说:‘这不可能,你的父亲不是工程师,你的母亲也不是,他们不会录取你的。’”萨扬回忆说,“她回答我:‘不不,在这里,你可以学习任何你想要学习的。’”这句话对他犹如醍醐灌顶。他转学进入佛蒙特大学。在那里,他生活在一户美国人家中,他录下所有的课程,因为他几乎听不懂授课的语言。每天晚上,寄宿家庭的母亲会帮助他一起整理录音。
就像当初他打定主意上小学,作为逃离工厂的紧急出口一样,现在他决定去癌症实验室当志愿者,于是他发出一封又一封的邮件。“无人回复。我对自己说:‘好吧,他们都是大忙人,那我就只能去敲门了。’”他说,“我以前就这么干过,所以我还能再做一次。”最后,他成功在实验室会议上搭上了一位研究人员,后者正好在研究土耳其中部由矿石沉积引发的间皮瘤,很有兴趣招一个会讲土耳其语的同事。
最终,一切从实验室里得到了回报。萨扬分析间皮瘤细胞如何对化疗产生耐受,以及鸡尾酒靶向药物如何缓解化疗耐受。“这是我得以进入医学院的原因之一。”他说,不过毕业时加入美国大学优等生学会和拿到最优等成绩当然没有坏处。他还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冰冻的池塘上胡乱滑行,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开始练习花样滑冰,而后来在佛蒙特还当过滑冰教练。
到了开始成为住院医师的时候,他早已设想好展开怎样的研究。他在佛蒙特大学招募脑癌患者,想要理解为什么这些患者会经历长期疲劳。
他还想在新泽西研究这个问题。对于那里的放射肿瘤学家来说,这标志着萨扬不是他们常见的那种培训生。正如罗格斯癌症研究所放射肿瘤科主席布鲁斯·哈夫提(Bruce Haffty)说:“一个医学生已经展开临床实验研究,而且还是自己提出的课题,这点相当与众不同。”
对萨扬来说,研究也是为了自己。在学位、奖学金、论文发表这一个个成就之下,流淌着悲痛之情。萨扬高中毕业时,父亲过世了,但那个他儿时记忆中的男人其实已经走了好多年。在疾病和治疗之间,父亲已成为了某种幽灵般的存在。“在伊斯坦布尔,我不记得和他有过任何美好的回忆。”萨扬说。
这也是他对于疲劳乏力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他看到脑癌患者不仅在化疗过程中被疲劳和乏力步步拖累,而且在一些病例中,治疗结束后这种症状还会持续很久。他想要知道确切的原因。问题出在肿瘤还是治疗手段?如果他能指出谁产生了怎样的感受,以及为什么,那也许能够消除那种感觉,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

图片来源:Pixabay
“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我们把它归咎于治疗和肿瘤。”萨尔玛·贾布尔(Salma Jabbour)说,他是罗格斯癌症研究所的胃肠道放射肿瘤科主任,“想要研究这个问题,表明你很关心患者正在经历的状况,这令人记忆深刻。”
临床试验不是研究中唯一让他想起自己父亲的部分。当他开始研究是否有可能安全地合并乳腺癌疗法,进行次数更少的治疗而每次强度更高时,他发现问题不仅在于生理学方面,也关系到经济方面。
“传统的乳腺癌治疗大约持续五到六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么长的治疗时间。”他说,“佛蒙特是大城市,让我们忘掉佛蒙特,在土耳其……”
他恰好知道,跋涉去接受治疗的旅途会多么艰辛,治疗的持续时间或者价格可能会决定患者的命运。
他当然知道代价有多少。他的姐妹们最终都结婚了,但母亲继续在同一家T恤工厂工作,直到他医学院毕业后开始挣钱。“有了第一份工资支票,我开始每个月给我母亲寄钱。”他说,“她终于不用再去那家工厂工作了,我好开心。”
萨扬频繁地返回土耳其,不仅是为了探亲,同时也是为了研究。两年前的夏天,他往返于马尔丁、加齐安泰普、哈蒂和梅尔辛之间,收集定居在那些城镇及其周边的叙利亚难民中的癌症患病率数据。他发现,极少有人接受放射性治疗(放疗),而那些接受放疗的人中也有许多会错过预约(没有完成治疗),这降低了他们的存活率。萨扬说,护理本身是免费的,就像医疗口译服务一样,但他想知道问题是不是在于时间或者交通。
对某些人来说,某些疗法并没有普及到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中,这可能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种情况让萨扬很担心,就像为任何阻挡治疗的障碍担心一样,无论患者来自哪里。
人们很容易想象一个在某种“真空环境”中展开的癌症研究,科学努力延长患者生命,远离地缘政治和政策的喧嚣。而想到谁来收容寻求庇护的人和难民,谁来将他们拒之门外,什么样的政策能提供良好的护理,这些问题就让人不那么舒服了。萨扬的故事是一种抓住机遇的教育范本,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我们都想在他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头脑聪颖,个性温厚,风趣健谈,不知疲倦地追求某种深刻的道德和价值。我们从来不会想象自己成为某个工厂主,对于手下员工受伤流血的情况视而不见。
作者:Eric Boodman
翻译:阿金
审校:戚译引
引进来源:ST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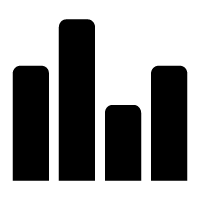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