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Martin Bollazzi
在昆虫界,蚂蚁因其复杂的社群结构和社会行为而闻名。工蚁和觅食蚁供养着它们的蚁后,为了整个种群的健康发展忠实地履行着它们的社会角色。正如科学家所称,由整个蚂蚁群构成的复杂的“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已经成为探索社会有机体的遗传和行为根源的主要模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蚂蚁群中也有极个别的特例。有些蚂蚁不太合群,也不履行自己在群体中的社会责任,而是混迹于它们的亲戚中,成为一群蹭吃蹭喝的“寄生蚁”。
近日,在一篇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最新研究中,一组欧美研究人员联手收集并探索了这群罕见的“寄生蚁”。该国际合作项目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主导,参与者包括来自德国明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Münster)、丹麦哥本哈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以及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大学(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的研究人员。他们共同获得并分析了罕见的“群居寄生蚁”——属于切叶蚁亚科的Acromyrmex inquilines——完整的基因组DNA序列,以更好地了解它们与宿主种群之间的差异。
这也是首次对群居寄生蚂蚁的基因组进行测序。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Christian Rabeling表示:“这是一个了解新的、高度特化的生命的过程,我们的发现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些生物基因组的理解,并为蚁群的群居寄生现象的演化过程提供了详细的见解。”
从“群居”到“群居寄生”
了解这种不同寻常的转变至关重要,因为蚂蚁的基因组已经进化了一亿多年。在此期间,蚂蚁社会出现了一次重大转变,即转变为具有工蚁等级和无条件利他行为的全新“超有机体”社会组织结构。采取这种“超有机体”模式的蚂蚁在演化上非常成功,蚂蚁共有17个亚科、338个属和13,900多个现存物种。

图片来源:Pixabay
Rabeling说:“物种向高度特化的群居寄生行为转变、并且放弃源于祖先的日常生活方式,通常都是基于远交(outbreeding)现象和更大的有效种群数量。我们能通过基因组的改变来了解这种现象,对其中三个物种的分析结果证实,我们能从蚂蚁群居寄生的现象中识别合作群居群体生活的特征。”
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分析证实,在大约一百五十万年的时间跨度中,这些蚂蚁物种都为自己找到了独树一帜的进化方式,并成为了群居“寄生蚁”。研究发现,在群居寄生蚂蚁中,全基因组会出现最为极端的特定性状的遗传侵蚀(genetic erosion)现象。
那它又是如何开始的?一群蚁后想要生活在一个蚁群中并坐享其成,不再为这个蚁巢付出任何劳动。接下来,蚁后只专注于生产新的蚁后和雄性蚂蚁,而这一小群“寄生蚁”能通过频繁地近交(inbreeding)得以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基因组的多样性也会急剧下降。然后,在未来进化过程中的某一瞬间,由于自然选择和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发生率的增加,祖先性状的丢失率因而提高,更具适应性的新性状出现的速率也会减慢。
这就是说在“寄生蚁”的DNA中出现了丢失,由此触发了基因组侵蚀(genome erosion)现象。
为了在蚂蚁基因组中证明这种效应,研究小组调查了整个基因组结构,以及可能受该基因组衰变影响的单个基因。首先,他们发现了基因组重排和倒置的广泛证据,这是基因不稳定和衰变的标志;其次,在基因网络中,研究小组鉴定了233个基因,这些基因在至少一个“寄生蚁”分支中表现出疏松选择(relaxed selection)的迹象,另有102个基因表现出强化选择(intensified selection)的迹象。Rabeling补充道:“我们的分析表明,这四个‘寄生蚁’进化分支点中有三个发生了基因家族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另外一些基因的丢失。”
基因组丢失和减少,对“寄生蚁”的嗅觉和味觉影响最大。
失败的嗅觉能力测试
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的不仅仅是负责蚂蚁嗅觉的基因。当研究者进行显微CT扫描时,还发现蚂蚁的大脑嗅叶(olfactory lobes)也缩小了。
对这一现象,Rabeling解释说:“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蚂蚁们主要通过化学信号进行交流。嗅觉基因的丧失与广泛存在的形态和行为的极端转变有关。”

图片来源:Pixabay
这包括工蚁等级制度的减少或完全丧失,口器、触角、体壁的简化,某些内分泌腺体的丧失,以及神经系统的复杂程度降低——这一点可能与急剧缩小的行为模式有关。
从他们的分析比较中,研究人员还通过更为长远的进化时间尺度来理解这些变化。他们还能以此确定切叶蚁谱系中“寄生蚁”的起源。
蚁属Acromyrmex中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寄生蚁”起源。在这个属内,一种群居蚂蚁A. heyeri是“寄生蚁”A. charruanus和P. argentina的寄主物种。
首先,在两类“寄生蚁”A. charruanus和P. argentin趋异之前,南美群居蚂蚁A. heyeri从它们共同的祖先中分离了出来,这一祖先也被认为是一种群居寄生蚁。
在演化上,这两个群居寄生现象属于近期发生的。据估计,约在250万年前,A. heyeri从A. charruanus和P. argentina最后的共同祖先中分离出来;约在100万年前,A. insinuator和A. echinatior发生了趋异现象。
Rabeling对此作出了推断:“松散的自然选择加速了群居‘寄生蚁’基因组侵蚀,并缓和了进化限制(evolutionary constraint),从而促进了与群居寄生生活方式相关的特定特征的快速适应性演化。”
探索的乐趣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进行基因组分析?事实证明,该研究中最容易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基因组分析;而找到蚂蚁则被证明是最大的障碍。这是为什么?
群居“寄生蚁”的种群几乎无一例外地小而分散。但有多分散呢?
他们在野外发现一种叫做P. argentina的寄生蚁物种是在1924年。Rabeling还记得,在此之前,由于找不到P. argentina,去南美的旅行总是徒劳而返。而后,大约在十年前,一通来自Martin Bollazzi的电话改变了他的生活,Bollazzi既是他的同事,也是后来这项研究的合著者。
“Martin Bollazzi说,他的妻子Leticia刚才居然发现了P. argentina!!!”
Rabeling在听到消息后急不可耐地跳上飞机。当他近距离看到寻觅已久的P. argentina时,他说那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Leticia所发现的P. argentina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探索成果。我特别喜欢将蚂蚁的野外工作和博物学观察与诸如全基因组测序等新技术联系起来,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真是太让高兴了!”
现在,他们可以通过收集P. argentina来实现他们的研究梦想,并通过对群居“寄生蚁”进行首次现代全基因组测序来验证他们基于野外工作而建立的假设。
下一步是什么?
这项研究的结果不仅对了解蚂蚁非常重要,还为在其他寄生物种中基因组“功能失去”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并在表型和基因组层面上识别合作、群居种群的生活特征。
Rabeling认为:“群居‘寄生蚁’的出现,是为了利用它们宿主的觅食努力、护理行为和群体基础设施。”
Rabeling还指出,其他物种,如墨西哥洞穴盲鱼(Mexican blind cave-dwelling fish)或绦虫(tapeworms)等其他寄生物种,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重要特征的生物。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都开发和利用了新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以使它们的物种得以生存。
研究人员表示,从这三种群居寄生蚁中,他们学到了很多。接下来,他们计划对这些群居寄生蚁进行基因组学研究,以获得令人兴奋的深入见解,特别是借助长读测序技术(long-read sequencing technologies),可以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不过,由于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蚂蚁自然栖息地因砍伐森林和发展而消失,Rabeling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已卷入另一场与时间的竞赛。现在,我们对蚂蚁进化的理解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拯救生物多样性。
“我们希望,这样的前瞻性研究能够扩大我们对蚂蚁社会行为演化特征的认识,毕竟很少有其他模型系统能够提供几十个物种水平的样本规模。”
翻译:许楚楚
编辑:魏潇
引进来源: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本文来自:中国数字科技馆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科普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其它相关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责任编辑:环球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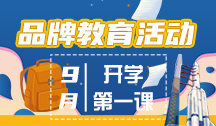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