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研究基因的专家组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可以允许编辑人类基因以防止遗传性疾病遗传给后代。
今年2月14日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and Medicine)发布了一项报告建议支持基因编辑,报告指出,改变生殖细胞的DNA,例如卵子,精子,受精卵或产生它们的细胞,可以治疗后代的遗传性疾病,但它只能用于改善疾病或残疾,不能用于增强人类的健康或者能力。这项决定与先前人类基因编辑全球峰会中组织者们的意见相反,他们认为使用像CRISPR/Cas9这样的分子剪刀进行基因编辑不应该用于生产婴儿。
该专家小组的联合主席,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aw School)的生物伦理学家Alta Charo表示,遗传基因编辑目前还未准备好应用于人类,他说:“我们不想为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开绿灯。我们正在试图寻找这项技术有限的适用条件,使它能在迫切的需求下被合理应用,并只用于满足这类需求。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不具有立法权,但它经常会影响美国和国外的政策决定。是否执行该建议将取决于美国国会、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监管机构,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新基因工程技术的支持者们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发言人 Sean Tipton说“相比于伦理问题,我们更看重基因编辑的使用可以消除一些遗传性疾病,这也是这项技术发展的初衷。”囊性纤维化和亨廷顿氏舞蹈症等疾病都是由单基因突变引起的,未来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矫正它们。但对于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由多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可能不会成为这项技术使用的重点。
还有些人担心,允许任何对生殖细胞的修补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设计婴儿”和其他社会问题。批评家们说,基因编辑增加了残疾人对羞辱的恐惧,加剧了负担得起与负担不起这样治疗的人群间的不平等,甚至担心这是一种新的优生学。
位于美国加州伯克利的美国遗传学与社会中心(Center for Genetics and Society)执行主任Marcy Darnovsky说:“一旦你赞成任何形式的人类生殖细胞修饰,你将打开它所有形式的新大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Panelist Jeffrey Kahn表示,遗传基因治疗的大门在严苛的要求被满足前仍是紧闭的,他在这份报告的公开演讲中讲到:“坦白的说,这项决策更像是在敲这扇门。”
Darnovsky说,“我在他们的推荐中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失望。”这份报告还将争论从是否应该允许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转到该技术使用中如何划分治疗与增强人类能力。
在美国、中国与其它多个国家已有几项临床试验完成了对患有癌症或其它疾病的患者进行人体基因编辑。但这些治疗方式并不涉及对生殖细胞的改变,而是在其它机体或人体细胞内修复缺陷或改变其DNA。专家小组建议,这种体细胞基因编辑疗法也应被限制于治疗疾病而非增强人体功能中。
英国、瑞典和中国的研究人员们已经在实验室中完成了人类早期胚胎的基因编辑。最近在墨西哥与乌克兰完成的“三亲婴儿”临床试验也被视为是对生殖细胞的改变,因为该婴儿携带少量卵子捐赠者的DNA。但是储存这些孩子遗传特性的核DNA没有被改变。
目前,美国的研究人员们被严令禁止进行可能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的临床试验,无论是使用基因编辑还是制造三亲婴儿。这项新的建议为允许这样的实验铺平了道路。
但是专家小组列出了许多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进一步发展时需要清除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无法克服的。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市杜克法学院的一位生物伦理学家Nita Farahany说:“有些人认为基因编辑的要求非常严格,其风险可能永远大于益处。”
例如其中的一个障碍是基因编辑需要对接受该技术治疗的儿童进行多代追踪以确定这种治疗方式是否可以影响后代。但研究人员们可能永远无法保证他们能够进行这样长期的研究,Farahany说:“你无法将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们绑定在该研究上,让他们同意被跟踪研究。”
治疗与增强人体功能的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将CRISPR/Cas9技术用于多种研究的哈佛大学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表示,研究人员们可能也无法为两者之间画上一条让人信服的界线。他指出,几乎所有的医学成就都被认为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他说:“疫苗对于我们祖先来讲就是进步。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们的祖先,他们可以无需任何担心走进天花病房,那就像拥有超能力一样。”
Charo表示,比起药物,基因编辑可能更难增强人体功能。这项新技术非常精准却具有特定性,不携带致病突变的人可能不会受益于此。
翻译:闫亢
审校:张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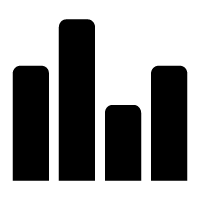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