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有孩子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整个学术圈对女性事业进步的不公。
在生命开端,同时也是最脆弱的阶段,上帝便赋予了女性生命创造者与守护者的职责。为了种族的延续,从怀孕到分娩,再从中恢复身心健康,紧接着,还有母乳喂养,建立与孩子的情感联系,照顾孩子,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事,都成为了她们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是女性生命的全部,她们还有其他的追求。不幸的是,在有些社会中,养育一个孩子却成为了女性追梦路上的阻碍。
我是一个科学家,一名教授,科学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两个可爱孩子的母亲。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需要出席许多会议。这也注定了在我的孩子出生后,我并不能一直陪在他们的身边。所以,我只能利用吸奶器储存母乳,也因此萌生出了评估母乳室的偏好。我发现从母乳室中可以看出一个组织的许多方面。比如说,一个为需要哺乳挤奶的出席者提供了整洁,私密,舒适空间的组织,总给人一种“我们重视家长,也体谅他们看护孩子的需求”的感觉。相反的,一个压根没准备,或只是敷衍了事的组织,则给人一种截然相反的感觉。
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当然,一路走来,我的所见所闻与亲身经历,也使我熟谙其他的一些女性面临的职场挑战,比如说,性骚扰和性别歧视。还有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揭示了养育一个孩子对女性的事业进步是多大的阻碍。为了与这不公正作斗争,我主动出击:参加了许多支持女性从事科学事业的会议和研讨会,在各种委员会下工作,以此来强调女性从事科学事业的重要性,并通过参与各种援助计划来支持女性的科学事业。
作为一名美籍墨西哥人,我对一些发生在弱势群体中女性身上的双重的不公正现象特别敏感。由于我的白皙肤色和与之伴生的特权,我见证了许多种族歧视的对话和决策,而谈话者和决策者却没发现我正是他们谈论的对象。
然而在有孩子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学术界对女性的不公。
从开始组建家庭的那一刻起,我们中的许多人就不得不面临一些健康问题,包括恶心,神经疼痛,下背部疼痛,脱水,贫血以及极度疲倦。然而在美国,我们在工作场所得到产前协助极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公司开出的产假,无论带不带薪,都远远不够。另外,产前的医疗护理也严重缺失。这根本说不过去。尽管许多研究一再强调,母亲的身心健康对妈妈和宝宝都是极其重要的,而相关政策还是有不妥与缺失。这是多么不合逻辑,目光短浅的表现啊。
而就我自己的经历,我的产后医护仅仅只有一个简略的体检,以及一份心理问卷调查,以此来衡量我产后抑郁的程度。然而这一切却只给出了类似“多睡觉”,“多喝水”以及“尝试约见心理医师”的建议。
我可以告诉你,当我用开裂带血的乳头喂奶的时候,我只能咬牙,强忍着疼痛坚持下去,因为没有一个医生或者哺乳专家能想出办法来改善这种情况。而这情况最终迫使我比计划提前结束母乳喂养。这一度让我沉浸在失落,愧疚和抑郁的情绪中。而每当我打开一罐奶粉,脑海中就浮现出公众那强盗般“母乳最好”的呼声,自以为是又带羞辱性地在耳边一遍又一遍响起,简直是雪上加霜。
我可以告诉你一次流产有多么痛苦。后来,由于医生拙劣的技术,剖腹产使我患上了创后应激紧张,在当时也没有经过诊断和治疗。这一点一滴的痛苦,积水成渊,最终导致了我的焦虑性障碍,以至于在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怀疑,也许没有我,我的家人会过得更好。
我可以告诉你,社会寄予既有家庭又有事业女性的期望有多么不公平,要好像没有家庭般工作,没有工作般照顾家庭。这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Schrödinger’s cat),在个人,专业和社会的层面上不公平的同时,也是毁灭性的。
我孩子们年纪还小,所以许多创伤都还记忆犹新。当我跟进自己的项目,教我的学生,尝试做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的社会成员时,他们仍无形地压在我的肩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有的时候,开教师大会期间我就望着同事们的脸,想象着他们其实又面临着怎么样的烦恼与压力。这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然而无独有偶,这种创伤和故事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只是很多需要工作的母亲中的一个代表而已。
作为一位女性,一名科学家,以及现在,一位母亲,我跻身在一个专为白人男性设计的体系当中,却不想他们一样,家中有一位全职照料家事的伴侣。这必然会生出许多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被迫就是自己决定换一个更轻松的行业。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科学行业!”,诸如此类的呼吁。我就心想: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也想成为科学事业的一份子!但是当我们必须付出男性同事的双倍努力,忍受家庭的牵绊和圈内的偏见,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时,这一切梦想都变成了幻想。
有的时候,人们会问我,我为什么还要待在一个如此“仇视”女性的行业里呢?我总会提醒他们,时代在变,尤其是在有些地方。同时,并不是只有科学界,学术界才有性别歧视的踪影。我从事法律,商业和娱乐业的朋友,都有在工作场合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使我震惊。但我们中的大多数还是选择留在原先的行业里,决心战胜追梦道路上的阻碍,扭转不利的局面。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她们的努力下,我们向前的动力更加明晰。向我们身后那些甚至更为不幸的人伸出充满希望的援手。
几个月前,我横穿全国到国家另一端去参加一场科学会议。对我而言,如果说科学是一座小镇,会议就是小镇的中央广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来到这场会议,来展示各自的科研成果,学习一些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分享新奇的想法并展开合作,寻找灵感,会面出资单位,招收实习生,找工作,总的来说,就是要成为更大团体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我一直对这类会议怀有好感。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怀孕,哺乳,照顾孩子的问题与责任,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困难了。不过此时此刻,就针对这场会议来说,怀孕和哺乳不再是困扰着我的问题了。在这里,我的角色只是我深爱机构的教师一员,领着可观的薪水。
我的丈夫,同时也是一名新进的教授,此时正在家中,在与我们终于能负担得起的可靠的日托所的合作下,照顾我们的孩子。我靠在会议中心的一面墙上,沐浴在从窗户流泻而下的阳光里。我深吸了口气,呷了一口热茶,然后如饥似渴地浏览着科研项目。是的,我活了下来。我回来了。
在讲座和海报展示之间,我到处走动,寻找着这儿的母乳室。虽然我不再需要它了,我还是很好奇它与前几年相比有没有改善。上次,当我想要去母乳室的时候,发现它离会议大厅远得离谱。大多数还在哺乳期中的母亲,为了能及时赶上她们的演讲,都放弃了走那朝圣一般的路程,而是在附近的角落中喂她们的孩子,或在卫生间挤奶。在卫生间挤奶是一件十分恶心的事情,这也是我曾经写过的一点。你会想要卫生间里做的饭吗?
当我继续探索的时候,我可喜地发现儿童中心可以使用。这无疑对于那些带着孩子来的会议参与者是很有帮助的。尽管如此,那些在事业敏感期的人—比如说研究生,博士后和新教员——同时也是最需要这类服务的人,往往却无法负担这类服务。当我还是个博士后的时候,我连参加会议时孩子的那张机票都负担不起,更不用说到了那儿以后的看护费了。
我发现母乳室离主展厅很近,相较往年确实是一个大的进步。我轻轻的推开门,不想打扰里面的妈妈们。出乎意料的是,这宽敞,地理位置又极好的房间却空空如也。走近一看,我恍然大悟。里面只有三挂弹出式窗帘,一把标准的会议椅,一张换尿布的桌子,以及一些散落的延长电线。一个在我所属领域中有着最高会费的会议,参与者高达数万人,同时有着上百场关于孕妇保健的演讲,为有哺乳需求的参与者所能提供的,竟只有这些吗?
不自觉的握紧拳头,鼻翼微张,我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希望能够冷静下来。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仅仅为了母乳室的事情大发雷霆有些不理性。但对于我而言,这些简陋敷衍的设施都代表着女性在这个国家的待遇。它们代表着我有了孩子之后还要在已经竞争激烈环境中尝试取得成功时,身心上受到的折磨。
而每当想到我那还在科学事业中,尝试在不平等的世界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姐妹们,我心中便涌现出一股母亲般的保护欲。在那一刻,我丝毫感觉不到对报复的恐惧,公开号召举办会议的组织提供更好的设施。我用社交媒体作为我的扩音器,把那些微薄敷衍的提供设施暴露在公众的眼睛之下。与此同时,其他的母亲,家长和我们的盟友也一并呼应,发出他们自己的照片,发表自己的不满,要求有所改变。
我找到了会议总部的一个代表,并向他们提了一些改进的建议。比如说,我建议大会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些有实际哺乳经验的人,或者专业的哺乳顾问。针对当时的情况,我还建议了一些简单迅速的方法,让哺乳期的母亲能舒适一些。
仅在一小时内,那些乱七八糟的电线就被整理好了,小小的会议椅被换成了舒适的大沙发,窗帘外面外加了一个休息室,另外还有几张桌子。那天晚一些的时候,我又回去看了一眼。灯光变得更加柔和,环境也舒适了许多。房间里有了几个女人坐在沙发上,显得很放松,要么在挤奶,要么在照顾孩子。环境安静平和,只有呼哧呼哧的挤奶声不时从里面传来。我笑了,一阵小小的治愈性的释怀和成就感涌上心头。一个正穿蓝色护理外套的女人与我刚好四目相对,相视而笑。
这时,我如梦初醒。会议组织者其实是真心想要帮助正在哺乳的出席者的——或至少想要避免不良影响。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得开始列出所有可能的方法,让会议更适合有家庭的人,尤其是对于在职母亲,并说明为什么这是有利于所有人的。
同时我也忽然意识到这些建议只来自于我自己的经历和观点,于是我号召群体的力量,希望能集思广益,解决会议照顾孩子的难题。我组织了一个由四十五个科学界中的母亲组成的工作小组,其中有博士后,助理教授和终身任职教授,以及在工业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们,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的成员,科学杂志编辑,和一位医学博士。另外,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是美国科学界中,话语权不足的群体的成员。我把我的手稿上传到云端上,实时地看着我的共同起草人进行编辑,提供建议和改进。
经过几周支持性的,发人深省又成果颇丰的各种活动,我们轻易地在最后对终稿达成了共识。期间,我们商议出了许多细节,希望会议不论大小,不论经济实力雄厚还是微薄,都可以帮助已为人父母的出席者,尤其是母亲。我们把自己的文章提交给一家顶尖的科学杂志社,希望可以接触到广大的读者。这家杂志甚至专门有一块栏目,是关于一些科学与社会的交叉话题的,有着影响政策的潜力。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却收到一封密封的拒收通知,称我们的文章并不适合他们的专栏。
虽然有些震惊,但我们的决心和勇气并未因此减少。于是我们又向另一家杂志社提交了文章。如果被拒,就再投下一家。在过去,这些杂志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的数据十分令人沮丧,它们表明,与男性以及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相比,职场母亲有很大的劣势。讽刺的是,现在有四十六位女性科学家聚在一起,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一个,他们竟对我们的呼声充耳不闻。
虽然屡遭拒绝,但在毅力与恒心的支持下,我们越挫越勇。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拒绝我们文章的编辑们——那些决定什么文章能发表的人——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对实际体验的缺乏,影响了对我们作品的评估呢?作为科学家,我们深知相关的事物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却能引起人的猜想。在这里,它启发我们,我们需要更多女性出现在高层编辑中,为这个问题带来更多的视角和解决方式。
当我们的文章终于被接纳时,编辑却提出了附带条件。有些编辑想要一些充斥着个人苦痛挣扎与泪水的故事。还有一些编辑希望我们文章的长度能缩短一半以上,那意味着我们必须缩略掉许多的建议。我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来自whatboutery的评论“那男人呢?那父亲们呢?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你们一起起草这篇文章呢?他们也是有所付出的啊!”事实上确实如此(还包括广义上的伴侣),首当其冲的就有我的丈夫,但我知道他会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人。如果有这么一天,男性必须经受分娩时的阵痛,承受身体被撕裂的痛苦,漫长疲惫地用他们自己的身体为孩子制造食物,而即便在付出了这么多之后,人们还是觉得女性做得更多,女性的报酬也更高,那我一定把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加到下一篇文章中去。而在那之前,一个真正的女性之友会帮助我们强调女性现在的煎熬。
最终,我们的文章在一位编辑(男性)的支持下,发表在《国家科学院的进展》(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中。当它被上传到网上时,我莫名的松了一口气,不仅仅是因为我希望会议能作出改变,还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经历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与寂寞无助。我想要那些妈妈们,或者那些马上想要孩子的女性们知道,我们四十六个人愿意为这个群体发声,要求有所改变。这不仅仅是为会议组织者提供的建议指导;也是我们通过将我们作父母的需求正常化而建立一个公正的工作环境的蓝图。
我是一位母亲,一名科学家,也是经受产后抑郁的幸存者。我决心帮助消除性别差异对待,为我的姐妹们铺平未来的道路。今天,我针对的是会议情况。明天,你会做什么呢?
关于作者:
Rebecca Calisi, 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神经生物学,生理学和行为学的助理教授,促进多元文化科学研究中心(CAMPOS)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环境健康科学中心(EHSC)的学者。
(翻译:费哲妮;审校:刘博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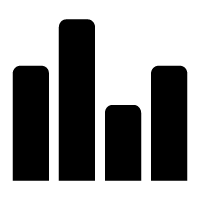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