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几岁时,父母经常带着我去超市里买东西。有一天,当我在耐心等待买单时,我的母亲拿出了她全新的顾客积分卡。出于好奇,我问收银员他们在积分卡上记录的是什么信息。他说,卡上记录了我们正在购买的东西,以便他们能够跟进我们购买的商品并量身定制产品推荐。我们之前对此毫不知情。我想,通过挖掘数以百万计的客户采购(数据),是否可能揭示隐藏的消费者偏好?很快我又意识到:他们是否因此向我们寄出了有针对性的广告?
这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但如今大多数人担心的问题与此并无太大差距:微目标信息的有效性如何?心理“大数据”是否足以影响你的产品购买力?或者,尤为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技术是否会被用作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例如选举结果的武器?一方面,我们接收来自内部人士的每日新闻,证明了基于数百万注册选民的独特“心理”特征,分析微目标信息的危险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像Brendan Nyhan这样的学术作家警告说,网络广告和“俄罗斯僵尸号”(类似于微博假帐号)的政治力量被广泛夸大了。
在试图评估心理科学对此的看法时,我认为关键是要理清两种明显的误解,这正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试图操纵公众舆论和真正的选民游说行为。反复发布迎合人们政治偏见的错误信息很可能会对公众态度造成影响,引起道德愤怒,并将党派分开,特别是当我们误以为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人都拥护同样的观点时。但是,这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了具体的投票行为呢?
事实上,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但是通过对已知信息的评估可以发现,经典的预测模型只包含社会人口数据(比如一个人的年龄),在预测行为方面并不是很有效。然而,将不同的人口、行为和心理数据拼凑在一起,比如你在Facebook(脸书)上点赞的页面,做过的性格测试结果,以及你的个人资料照片(可能揭示性别和种族信息)也可以用来提高数据质量。例如,在一项有5.8万名志愿者参与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发现,使用Facebook点赞的模型(平均170个点赞数的量级),进行了一系列预测,比如性别、政治倾向和性取向,准确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线上足迹实际上可以用来开展大众说服。通过共计350万人,横跨三项课题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根据人们心理量身定制的广告(即把一个有说服力的信息与一个人的广泛心理特征相匹配)会比不匹配的或非个性化的信息多出40%的点击量和50%的在线购买。这对心理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我们早就知道,量身定制的交流比千篇一律的方式更有说服力。然而,大规模线上说服的有效性可能会大不相同,而且对环境影响更加敏感。毕竟,网上购物和投票不一样!
那么,具有导向性的假新闻是否影响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呢?
政治评论家对此持怀疑态度,理由很充分:与一种新的洗发水相比,改变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要困难得多,许多关于政治说服的学术研究也都显示出该影响有限。其中一项关于人们暴露于假新闻下的研究,整合了156篇文章的假新闻数据库与美国人的全国性调查和结果,得出估计,在大选前,普通成年人只会接触到一篇或几篇假新闻。此外,研究人员认为,假新闻只能改变投票份额的一个百分点。然而,此研究中作者们主要依据受访者自己的回忆和针对15篇假新闻的汇报,而不是数字足迹。
相比之下,另一项针对个人浏览历史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大约25%的美国成年人(6500万)在选举的最后几周访问了一个假新闻网站。作者报告说,大多数虚假新闻消费都是支持Donald Trump的,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个小的意识形态小组。
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向585名之前支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选民展示了三种流行的假新闻(例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健康状况不佳,并批准向圣战者出售武器)。研究人员发现,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比如受访者是否喜欢克林顿和特朗普,在2016年的民主党竞选中,找出他们之中相信一篇以上假新闻的人要比找出其他选民(的准确率)高出3.9倍。因此,与其只关注对选民的劝说,这个相关的证据暗示了假新闻可能会导致选民被压制的可能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假新闻的目的往往不是让人们相信“另一个事实”,而是散布怀疑,并在政治上挑拨人们,这可能会破坏民主进程,特别是当社会的未来取决于投票偏好的微小差异时。
事实上,第二个常见的误解围绕着“小”效应的影响:小效应也能产生大影响。例如,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6100万人参与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向Facebook用户发送的政治动员信息直接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投票行为。重要的是,社会传播的影响大于信息本身的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研究中,选民的说服率大约是0.39%,虽然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却能获得282000张选票。如果你考虑一下主要的选举,比如英国退欧(51.9%对48.1%),或者希拉里最终以七万七千票的微弱优势输掉了选举,那么从背景上看,这样的小影响就突然变得非常重要。
简而言之,重要的是要记住,大众说服的心理学武器不需要建立在高度精确的模型基础上,也不需要在整个人群中产生巨大的足以破坏民主进程的影响。此外,我们只看到数据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很可能低估了这些工具的影响。例如,大多数学术研究都使用自我报告的调查实验,这些实验并不总是能准确地模拟在线新闻消费的真实社会动态。即使Facebook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低估了回声室效应的重要性时,这些数据也是用户(行为)的小缩影(数据源于那些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用户,大约占Facebook用户的4%)。此外,预测分析公司不会通过伦理审查委员会,或者一次使用一两个消息进行高度控制的研究。但他们每天耗资数百万在不同的受众上测试30到4万的信息,对算法进行微调,以细化所得信息,等等。
因此,由于缺乏透明度,模型的私有化性质,以及商业利益会过分强调或低估其有效性,我们必须在下结论时保持谨慎。大数据的兴起为社会和我的同事提供了很多潜在的好处,我也尝试过帮助建立在行为科学中使用大数据的道德标准,同时为人们注入和增强抵抗大众心理说服的思想和能力。但是,目前我们唯一确定的是,我们逐渐成为自己数字足迹的靶子,从书籍推荐到歌曲选择,再到你票选的候选人。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成为了不知情的参与者,参与着一个可能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为科学实验。
翻译:翁逸芳
审校:董子晨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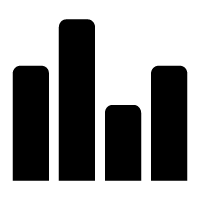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