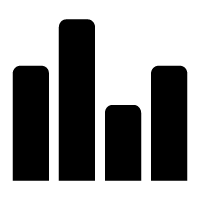最近几年,疟疾可以最终被消灭的希望越来越大,但是新的挑战打击了这种乐观的情绪。科学家们警告称一种“超级疟疾”病原体正在东南亚急速传播。该病原体对一线推荐药物青蒿素耐药。一旦它传播到非洲,将造成全球健康威胁。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国会有提案将“总统疟疾计划(PMI)”的支出削减44%,一旦通过,将给疟疾预防和治疗项目造成显著影响。数学预测指出对PMI的财政削减将导致未来4年有额外的300,000人口因疟疾死亡。
尽管疟疾还会是一个主要的全球健康隐患,疟疾的死亡病例已经开始下降,这主要归功于由PMI资助的疾控项目,例如分发经过杀虫药处理过的蚊帐、对室内遗留物品的的杀虫药喷洒、和抗疟疾治疗。2015年,全球因疟疾死亡的病例据估计有438,000,而2013年还有584,000。其中大多数(92%)发生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人担心一旦东南亚地区的耐药株扩散到非洲,目前取得的成果将会打折扣。
不幸的是,新的耐药株的出现和扩散对疟疾疾控专家来说并非偶然,这只是历史的重演。就像蚊子对杀虫药的耐药一样,疟原虫对药物的耐受也是我们曾经历过的现象,在疟疾最终被消灭之前,我们可能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因此,我们应该将周期性出现的疟疾耐药性视为学习新经验的机会,借此了解疟原虫和它们的传播途径、开发更加合适的疾控手段,使得新的替代疗法能撑过更长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再次加倍我们的投入,增加并维持疟疾疾控的经费。
耐药疟原虫株的传播是由疟蚊(当它们叮咬人类时,疟原虫会在不同宿主间传播)和全球化下的跨洋航空推动的。目前的疟疾疾控一线工具包括青蒿素混合药物治疗、睡觉时使用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和室内杀虫剂喷洒。这些都很有效,但是疟疾正是利用它们缺席的空隙传播的。为了让疟疾无缝可钻,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投入来维持并改善当前取得的成果,以建立日程,催生更完整的疟疾疾控系统。
“消灭疟疾”这个目标永远是一个移动的靶子。疟原虫和传播它们的蚊子总是随着疾控手段发生改变,要跟上它们变化的脚步,我们的方法和实践需要有动态性,着眼于鼓励多管齐下对抗疟原虫和蚊子的策略。 疾控也需要与社区接地:环境工作者和社区健康工作者可以从农业领域的“病虫害整合管理”行动中学到重要的经验。
疟疾涉及到人类宿主、蚊子载体和疟原虫。由于疟原虫生活史的一半在蚊子体内,一半在人类体内,这很自然地解释了目前的疟疾控制也对两条路径分别关注:第一是用蚊帐和杀虫剂减少人类-载体之间的接触,第二是通过监控和有效治疗来控制人口内部的疟原虫循环。
尽管这些一线干预的有些设想已经实现,我认为将它们与其它疾控手段以一种多学科的手段结合会最终产生叠加效应,可能会减小目前手段的漏洞,推进消灭疾病的进程。其中一种候选的疾控手段是蚊虫繁育地的消灭,作为“载体整合管理”框架的一部分,它要求社区的积极参与来加强可持续性。另一种重要的疾控手段是为社区健康工作者建立界定明晰的疟疾患者监控工具,辅助有效地诊断和及时的治疗。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疟疾已经被消灭,斯里兰卡的抗击疟疾项目成功了——即便是在这个岛国和印度之间人口持续流动,加上20年来战争和政治动乱的背景下——这都是因为多维度的措施:一个有效的蚊虫控制项目、一个三管齐下的疟原虫监控项目、还是一个“病人管理”或者说疾病治疗项目。现在的大问题是能否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建立相似的手段。现在的期望很高,因为斯里兰卡使用的工具都在手边。目前需要的是来自倡议者、政治意愿和适量经费的支持,协调地将这些工具整合到当地。因此,PMI经费削减提案只会让已经不好的情况变得更糟。上述提案必须被重新考虑。
对“超级疟疾”病原体从东南亚扩散的非洲的担忧是经过论证的。因此除了保证当地的疟疾整合控制外,也该强调对旅行者,尤其是亚非之间的旅行者的出行建议和药物预防。对一种抗疟疾药物的耐药性总是先在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中出现,通常是当地的婴儿和儿童( 免疫力必须在活过数次疟疾之后获得)和外来的成年旅行者。对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其它疟疾疾控的利益相关者来说,现在是很好的机会来巩固和引进新的国际旅行管控,规范疟疾防控药物使用,就像目前对黄热病等疾病的强制疫苗一样。
疟疾研究集体对探索疾控新手段的使命感更强,绝对不能在超级疟疾面前泄气。应对新的挑战可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和经费,但是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然而,要在眼前留住消灭疟疾的希望,我们必须吸取数十年来疟疾成功控制的经验教训,阻断超级疟原虫的传播,避免危机的发生。这可能是一场即将面对的新战役,而不代表我们输掉了整场战争。